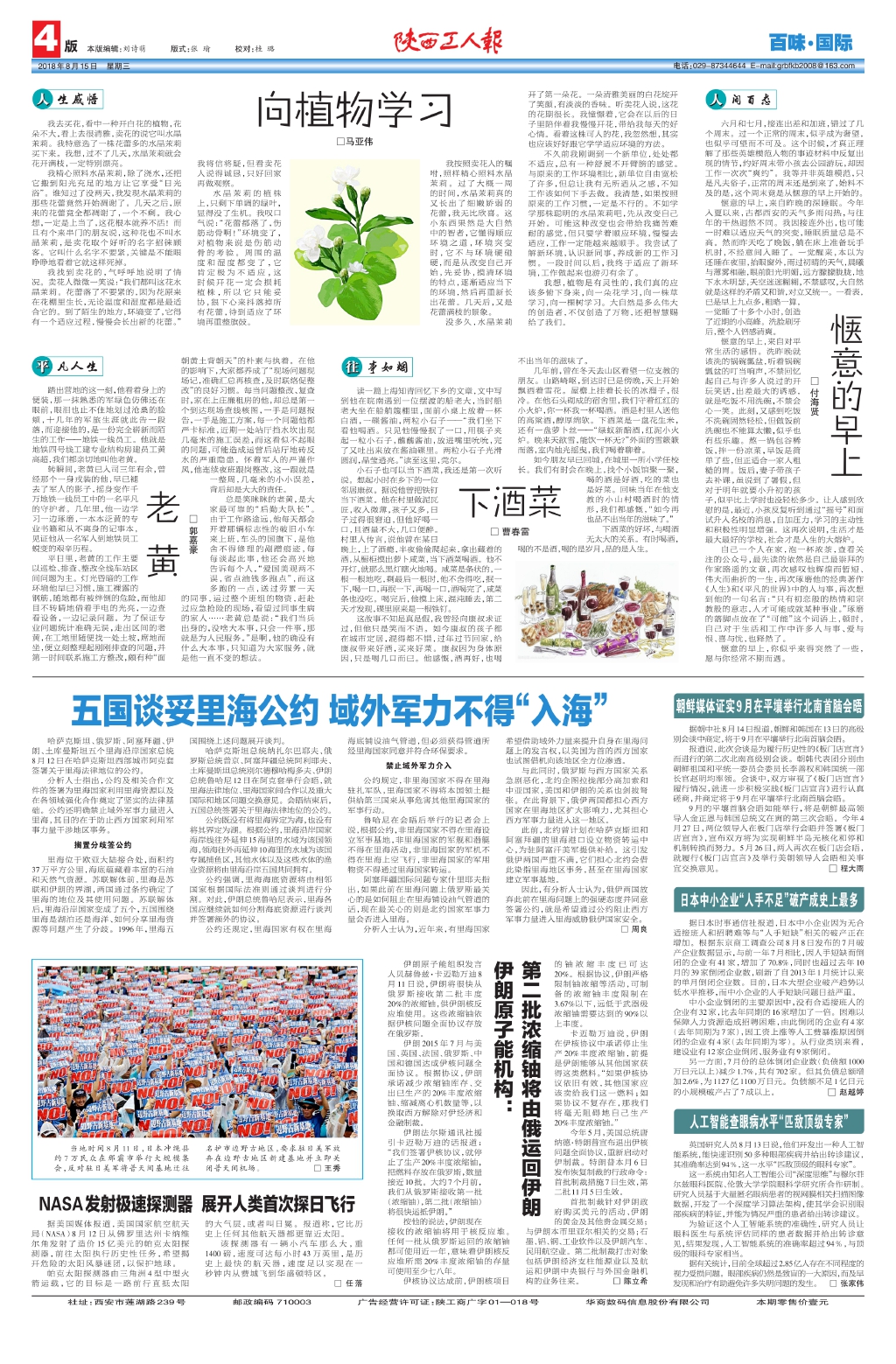下酒菜
□曹春雷

读一篇上海知青回忆下乡的文章,文中写到他在皖南遇到一位摆渡的船老大,当时船老大坐在船艄篾棚里,面前小桌上放着一杯白酒,一碟酱油,两粒小石子——“我们坐下看他喝酒。只见他慢慢抿了一口,用筷子夹起一粒小石子,蘸蘸酱油,放进嘴里吮吮,完了又吐出来放在酱油碟里。两粒小石子光滑圆润,晶莹透亮。”读至这里,莞尔。
小石子也可以当下酒菜,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想起小时在乡下的一位邻居康叔。据说他曾把铁钉当下酒菜。他在村里做泥瓦匠,收入微薄,孩子又多,日子过得很窘迫,但他好喝一口,且酒量不大,几口便醉。村里人传言,说他曾在某日晚上,上了酒瘾,半夜偷偷爬起来,拿出藏着的酒,从橱柜摸出萝卜咸菜,当下酒菜喝酒。他不开灯,就那么黑灯瞎火地喝。咸菜是条状的,一根一根地吃,剩最后一根时,他不舍得吃,抿一下,喝一口,再抿一下,再喝一口,酒喝完了,咸菜条也没吃。喝完后,他摸上床,混沌睡去,第二天才发现,碟里原来是一根铁钉。
这故事不知是真是假,我曾经向康叔求证过,但他只是笑而不语。如今康叔的孩子都在城市定居,混得都不错,过年过节回家,给康叔带来好酒,买来好菜。康叔因为身体原因,只是喝几口而已。他感慨,酒再好,也喝不出当年的滋味了。
几年前,曾在冬天去山区看望一位支教的朋友。山路崎岖,到达时已是傍晚,天上开始飘洒着雪花。屋檐上挂着长长的冰溜子,很冷。在他石头砌成的宿舍里,我们守着红红的小火炉,你一杯我一杯喝酒。酒是村里人送他的高粱酒,醇厚绵软。下酒菜是一盘花生米,还有一盘萝卜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外面的雪簌簌而落,室内烛光摇曳,我们喝着聊着。
如今朋友早已回城,在城里一所小学任校长。我们有时会在晚上,找个小饭馆聚一聚,喝的酒是好酒,吃的菜也是好菜。回味当年在他支教的小山村喝酒时的情形,我们都感慨,“如今再也品不出当年的滋味了。”
下酒菜的好坏,与喝酒无太大的关系。有时喝酒,喝的不是酒,喝的是岁月,品的是人生。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曹春雷

读一篇上海知青回忆下乡的文章,文中写到他在皖南遇到一位摆渡的船老大,当时船老大坐在船艄篾棚里,面前小桌上放着一杯白酒,一碟酱油,两粒小石子——“我们坐下看他喝酒。只见他慢慢抿了一口,用筷子夹起一粒小石子,蘸蘸酱油,放进嘴里吮吮,完了又吐出来放在酱油碟里。两粒小石子光滑圆润,晶莹透亮。”读至这里,莞尔。
小石子也可以当下酒菜,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想起小时在乡下的一位邻居康叔。据说他曾把铁钉当下酒菜。他在村里做泥瓦匠,收入微薄,孩子又多,日子过得很窘迫,但他好喝一口,且酒量不大,几口便醉。村里人传言,说他曾在某日晚上,上了酒瘾,半夜偷偷爬起来,拿出藏着的酒,从橱柜摸出萝卜咸菜,当下酒菜喝酒。他不开灯,就那么黑灯瞎火地喝。咸菜是条状的,一根一根地吃,剩最后一根时,他不舍得吃,抿一下,喝一口,再抿一下,再喝一口,酒喝完了,咸菜条也没吃。喝完后,他摸上床,混沌睡去,第二天才发现,碟里原来是一根铁钉。
这故事不知是真是假,我曾经向康叔求证过,但他只是笑而不语。如今康叔的孩子都在城市定居,混得都不错,过年过节回家,给康叔带来好酒,买来好菜。康叔因为身体原因,只是喝几口而已。他感慨,酒再好,也喝不出当年的滋味了。
几年前,曾在冬天去山区看望一位支教的朋友。山路崎岖,到达时已是傍晚,天上开始飘洒着雪花。屋檐上挂着长长的冰溜子,很冷。在他石头砌成的宿舍里,我们守着红红的小火炉,你一杯我一杯喝酒。酒是村里人送他的高粱酒,醇厚绵软。下酒菜是一盘花生米,还有一盘萝卜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外面的雪簌簌而落,室内烛光摇曳,我们喝着聊着。
如今朋友早已回城,在城里一所小学任校长。我们有时会在晚上,找个小饭馆聚一聚,喝的酒是好酒,吃的菜也是好菜。回味当年在他支教的小山村喝酒时的情形,我们都感慨,“如今再也品不出当年的滋味了。”
下酒菜的好坏,与喝酒无太大的关系。有时喝酒,喝的不是酒,喝的是岁月,品的是人生。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