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画里自洽于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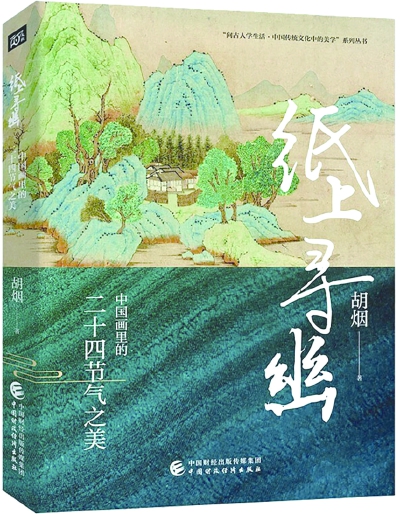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成果典范,它不仅是“天文之学”,更是“人文之学”,体现出中国古人独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美学。同时,这套知识体系也是充满无穷诗意的。比如,从字面来理解,“惊蛰”,就是把不吃不喝冬眠了一整个冬天的动物们都叫醒过来,迎接春天的到来,光听上去,“惊”字背后的那股春雷乍响的气象就营造着万物苏醒的热闹盛况,让人好不激动。
这种有关自然节律的科学认识还被古代先民投射到关于个体生命的认知中。除了各种文学、俗信、礼仪、节庆,中国古代的画家们用手中的笔,也生动再现了这种“因时而动,顺势而为”的哲学和美学。其中,又以中国文人画为甚。画家们多将自己内心的感悟寄托到笔下的人物、山水、花鸟鱼虫上,营造“意境”与“心境”。如郑板桥所说:“兰香不是香,是我口中气。”“兰花不是花,是我眼中人。”
在中国画里,二十四节气里的风物被赋予了鲜亮的生命力,从而具有了“人”的品格和情感指向,所以,其表现的是“人化的自然”“社会化的自然”,也是“活化的自然”。经过胡烟的《纸上寻幽:中国画里的二十四节气之美》解读,与二十四节气有关的中国画,其独特的文化象征、文化隐喻以及审美意象被无穷放大,便有了人味,也便有了活气和生意。
若是看《纸上寻幽》一书里胡烟的点评,会生发这样的感受:与其说顾恺之、王希孟、文徵明的画是文人画,倒不如说是人文画,是“灵魂的功课”。如果说古代画家们是借物抒情、借物言志,那么,《纸上寻幽》给我们树立了一个赏画的标准范式,即要聆听画外之音,捕捉画外之意——要穿过纸墨,去捕捉蕴藏在画里的生命寓意,以及恬静幽深的心灵宇宙。简言之,胡烟带我们在中国画里观看大美的天、地、人,释读磅礴的宇宙观、自然观、生命观,更重要的是,去捕捉画家们作为一个寻常人的幽微的真性情,穿越历史风云,解密古代画家植入画作中的人格象征、隐喻以及精神品性,从而读懂古人、读懂古画,也读懂如画的二十四节气。
比如,胡烟从杨无咎所作的《四梅图》里,首先感受到了以梅作喻的生命也有属于自己的四季轮回,她读懂了杨无咎表面上是借助清幽的梅花,来自许品格中的清高和疏淡之美,而往深了看,她看到了不想入仕的杨无咎无法理顺自我与环境的关系的痛苦所产生的“张力”传递到纸上后,所发出的“千钧一发的沉寂之力”。胡烟甚至小心翼翼地揣摩杨无咎是不是也如自己一样敏感,但她大胆地判断:“杨无咎的梅,是时刻想从宣纸上逃走的。”
心中有天地,笔下便有众生。以杨无咎为代表的中国画的作者们如此,胡烟亦如此。世间万事万物,包括二十四节气,本无感情,恰是因为欣赏它、表现它、歌颂它的人,有了万般情绪,才使其有了几多趣味。画,到最高境界时,已不是画,亦非技法,而是活生生的如巨澜奔泻的心潮,是方生方死的世间百态。画家们的真性情,恰如二十四节气,有时如春意喧闹,有时如寒雪沉静。
《纸上寻幽》,“寻”的是古人对四时的感应和再现,当然,“寻”的也是今人对情境的复现和再造、对情感的体验和超越,“寻”的是一种深度的心灵体验,寻的是一种高级的精神之“幽”——二十四节气何以如画,亦何以入画?胡烟将心与古人贴在一起。不!她似乎穿越了时空,摇身一变为古人,她就是金农、宋徽宗、郭熙、边寿民……从《纸上寻幽》里,我们读懂了文人画家们的自愈、自娱、自喻、自怜甚至自恋,赏得深了,便可会心一笑,也可怡然自洽。□潘飞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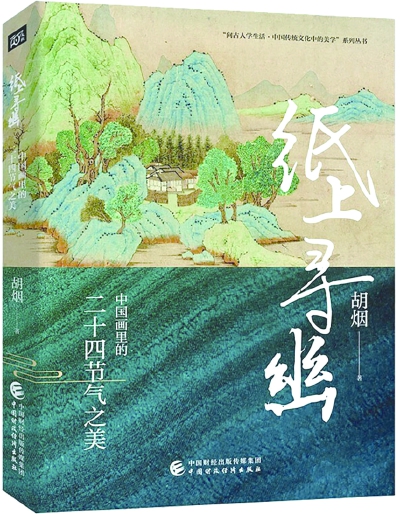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成果典范,它不仅是“天文之学”,更是“人文之学”,体现出中国古人独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美学。同时,这套知识体系也是充满无穷诗意的。比如,从字面来理解,“惊蛰”,就是把不吃不喝冬眠了一整个冬天的动物们都叫醒过来,迎接春天的到来,光听上去,“惊”字背后的那股春雷乍响的气象就营造着万物苏醒的热闹盛况,让人好不激动。
这种有关自然节律的科学认识还被古代先民投射到关于个体生命的认知中。除了各种文学、俗信、礼仪、节庆,中国古代的画家们用手中的笔,也生动再现了这种“因时而动,顺势而为”的哲学和美学。其中,又以中国文人画为甚。画家们多将自己内心的感悟寄托到笔下的人物、山水、花鸟鱼虫上,营造“意境”与“心境”。如郑板桥所说:“兰香不是香,是我口中气。”“兰花不是花,是我眼中人。”
在中国画里,二十四节气里的风物被赋予了鲜亮的生命力,从而具有了“人”的品格和情感指向,所以,其表现的是“人化的自然”“社会化的自然”,也是“活化的自然”。经过胡烟的《纸上寻幽:中国画里的二十四节气之美》解读,与二十四节气有关的中国画,其独特的文化象征、文化隐喻以及审美意象被无穷放大,便有了人味,也便有了活气和生意。
若是看《纸上寻幽》一书里胡烟的点评,会生发这样的感受:与其说顾恺之、王希孟、文徵明的画是文人画,倒不如说是人文画,是“灵魂的功课”。如果说古代画家们是借物抒情、借物言志,那么,《纸上寻幽》给我们树立了一个赏画的标准范式,即要聆听画外之音,捕捉画外之意——要穿过纸墨,去捕捉蕴藏在画里的生命寓意,以及恬静幽深的心灵宇宙。简言之,胡烟带我们在中国画里观看大美的天、地、人,释读磅礴的宇宙观、自然观、生命观,更重要的是,去捕捉画家们作为一个寻常人的幽微的真性情,穿越历史风云,解密古代画家植入画作中的人格象征、隐喻以及精神品性,从而读懂古人、读懂古画,也读懂如画的二十四节气。
比如,胡烟从杨无咎所作的《四梅图》里,首先感受到了以梅作喻的生命也有属于自己的四季轮回,她读懂了杨无咎表面上是借助清幽的梅花,来自许品格中的清高和疏淡之美,而往深了看,她看到了不想入仕的杨无咎无法理顺自我与环境的关系的痛苦所产生的“张力”传递到纸上后,所发出的“千钧一发的沉寂之力”。胡烟甚至小心翼翼地揣摩杨无咎是不是也如自己一样敏感,但她大胆地判断:“杨无咎的梅,是时刻想从宣纸上逃走的。”
心中有天地,笔下便有众生。以杨无咎为代表的中国画的作者们如此,胡烟亦如此。世间万事万物,包括二十四节气,本无感情,恰是因为欣赏它、表现它、歌颂它的人,有了万般情绪,才使其有了几多趣味。画,到最高境界时,已不是画,亦非技法,而是活生生的如巨澜奔泻的心潮,是方生方死的世间百态。画家们的真性情,恰如二十四节气,有时如春意喧闹,有时如寒雪沉静。
《纸上寻幽》,“寻”的是古人对四时的感应和再现,当然,“寻”的也是今人对情境的复现和再造、对情感的体验和超越,“寻”的是一种深度的心灵体验,寻的是一种高级的精神之“幽”——二十四节气何以如画,亦何以入画?胡烟将心与古人贴在一起。不!她似乎穿越了时空,摇身一变为古人,她就是金农、宋徽宗、郭熙、边寿民……从《纸上寻幽》里,我们读懂了文人画家们的自愈、自娱、自喻、自怜甚至自恋,赏得深了,便可会心一笑,也可怡然自洽。□潘飞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