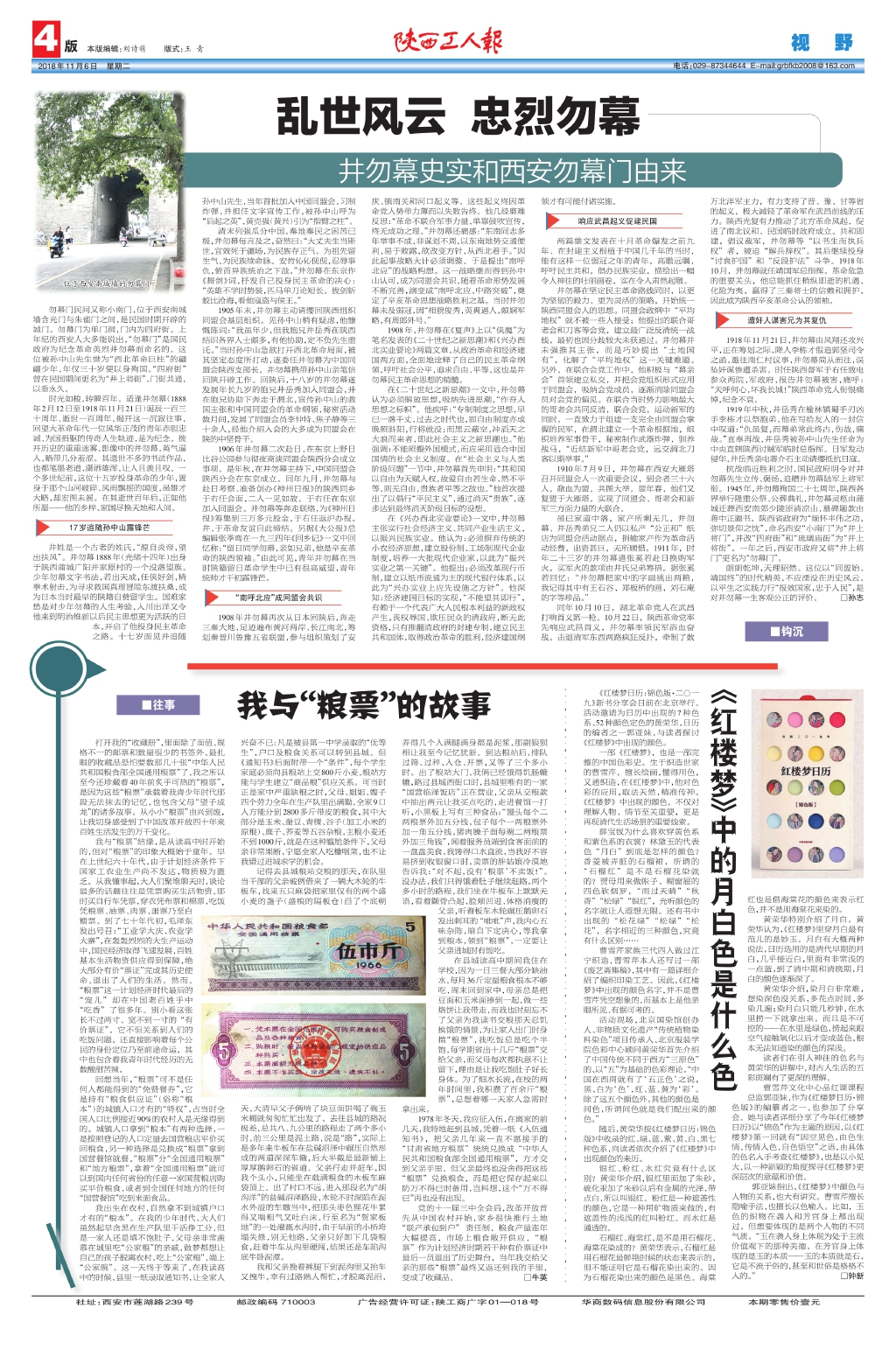我与“粮票”的故事


打开我的“收藏册”,里面除了面值、规格不一的邮票和数量很少的书签外,最扎眼的收藏品恐怕要数那几十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全国通用粮票”了,我之所以至今还珍藏着40年前炙手可热的“粮票”,是因为这些“粮票”承载着我青少年时代那段无法抹去的记忆,也包含父母“望子成龙”的诸多故事。从小小“粮票”由兴到废,让我切身感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百姓生活发生的万千变化。
我与“粮票”结缘,是从读高中时开始的,但对“粮票”的印象大概始于童年。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工农业生产尚不发达,物质极为匮乏。从我懂事起,大人们聚堆聊天时,谈论最多的话题往往是凭票购买生活物资,那时买自行车凭票,穿衣凭布票和棉票,吃饭凭粮票、油票、肉票、蛋票乃至白糖票。到了七十年代初,毛泽东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国民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百姓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得到保障,绝大部分有价“票证”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了人们的生活。然而,“粮票”这一计划经济时代最后的“宠儿”却在中国老百姓手中“吃香”了很多年。别小看这张长不过两寸、宽不到一寸的“有价票证”,它不但关系到人们的吃饭问题,还直接影响着每个公民的身份定位乃至前途命运,其中也包含着我青年时代经历的无数酸甜苦辣。
回想当年,“粮票”可不是任何人都能得到的“免费餐券”,它是持有“粮食供应证”(俗称“粮本”)的城镇人口才有的“特权”,占当时全国人口比例接近90%的农村人是无缘得到的。城镇人口拿到“粮本”有两种选择,一是按照登记的人口定量去国营粮店平价买回粮食,另一种选择是兑换成“粮票”拿到国营餐馆就餐。“粮票”分“全国通用粮票”和“地方粮票”,拿着“全国通用粮票”就可以到国内任何省份的任意一家国营粮店购买平价粮食,或者到全国任何地方的任何“国营餐馆”吃到米面食品。
我出生在农村,自然拿不到城镇户口才有的“粮本”。在我的少年时代,大人们虽然起早贪黑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但是一家人还是填不饱肚子,父母亲非常羡慕在城里吃“公家粮”的亲戚,做梦都想让自己的孩子脱离农村,吃上“公家粮”,端上“公家碗”。这一天终于等来了,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县里一纸录取通知书,让全家人兴奋不已:凡是被县第一中学录取的“优等生”,户口及粮食关系可以转到县城。但《通知书》后面附带一个“条件”,每个学生家庭必须向县粮站上交800斤小麦,粮站方能与学生建立“商品粮”供应关系。可当时正是家中严重缺粮之时,父母、姐姐、嫂子四个劳力全年在生产队里出满勤,全家9口人方能分到2800多斤带皮的粮食,其中大部分是玉米、蚕豆、青稞、谷子(加工小米的原粮)、糜子、荞麦等五谷杂粮,主粮小麦还不到1000斤,就是在这种尴尬条件下,父母亲非常果断,宁愿全家人吃糠咽菜,也不让我错过进城求学的机会。
记得去县城粮站交粮的那天,在队里当干部的父亲破例借来了一辆大木轮的牛板车,找来五只麻袋把家里仅有的两个盛小麦的盏子(盛粮的隔板仓)舀了个底朝天,大清早父子俩啃了块豆面饼喝了碗玉米糊就匆匆忙忙出发了。去往县城的路况极差,总共八、九公里的路程走了两个多小时,前三公里是泥土路,说是“路”,实际上是多年来牛板车在盐碱沼泽中碾压自然形成的两道深深车辙,后大半截是最新铺上厚厚鹅卵石的省道。父亲行走并赶车,因我个头小,只能坐在载满粮食的木板车麻袋顶上。出了村口不远,进入那段名为“胡沟洋”的盐碱沼泽路段,木轮不时深陷在泥水外溢的车辙当中,把那头枣色狸花牛累得又喘粗气又吐白沫,行至名为“贺家板地”的一处灌溉水沟时,由于早前的小桥垮塌失修,别无他路,父亲只好卸下几袋粮食,赶着牛车从沟里硬闯,结果还是车陷沟底牛卧泥潭。
我和父亲挽着裤腿下到泥沟里又抬车又拽牛,幸有过路熟人帮忙,才脱离泥沼,弄得几个人满腿满身都是泥浆,那副狼狈相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到达粮站后,排队过筛、过秤、入仓、开票,又等了三个多小时。出了粮站大门,我俩已经饿得饥肠辘辘,路过县城西街口时,县城里唯有的一家“国营临泽饭店”正在营业,父亲从交粮款中抽出两元让我买点吃的,走进餐馆一打听,小黑板上写有三种食品:“馒头每个二两粮票外加五分钱,包子每个一两粮票外加一角五分钱,猪肉臊子面每碗二两粮票外加三角钱”,闻着服务员端到食客面前的一盘盘美食,我馋得口水直流,当我好不容易挤到收银窗口时,卖票的胖姑娘冷漠地告诉我:“对不起,没有‘粮票’不卖饭!”。没办法,我们只得饿着肚子继续赶路,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们坐在牛板车上默默无语,看着颧骨凸起、脸颊凹进、体格消瘦的父亲,听着板车木轮碾压鹅卵石发出刺耳的“呲呲”声,我内心五味杂陈,暗自下定决心,等我拿到粮本,领到“粮票”,一定要让父亲进城时有饭吃。
在县城读高中期间我住在学校,因为一日三餐大部分缺油水,每月36斤定量粮食根本不够吃,周末回到家中,母亲总是把豆面和玉米面掺到一起,做一些烙饼让我带走,而我也时刻忘不了父亲为我读书交粮那天忍饥挨饿的情景,为让家人出门时身揣“粮票”,我吃饭总是吃个半饱,每学期省出十几斤“粮票”交给父亲,而父母每次都执意不让留下,理由是让我吃饱肚子好长身体。为了细水长流,在校的两年时间里,我积攒了百余斤“粮票”,总想着哪一天家人急需时拿出来。
1978年冬天,我应征入伍,在离家的前几天,我特地赶到县城,凭着一纸《入伍通知书》,把父亲几年来一直不愿接手的“甘肃省地方粮票”统统兑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全国通用粮票”,方才交到父亲手里。但父亲最终也没舍得把这些“粮票”兑换粮食,而是把它保存起来以防万不得已时备用,岂料想,这个“万不得已”再也没有出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首先从中国农村开始,家乡很快推行土地“联产承包到户”责任制,粮食产量连年大幅提高,市场上粮食敞开供应,“粮票”作为计划经济时期若干种有价票证中最后一员退出了历史舞台,当年我交给父亲的那些“粮票”最终又返还到我的手里,变成了收藏品。□牛英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打开我的“收藏册”,里面除了面值、规格不一的邮票和数量很少的书签外,最扎眼的收藏品恐怕要数那几十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全国通用粮票”了,我之所以至今还珍藏着40年前炙手可热的“粮票”,是因为这些“粮票”承载着我青少年时代那段无法抹去的记忆,也包含父母“望子成龙”的诸多故事。从小小“粮票”由兴到废,让我切身感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百姓生活发生的万千变化。
我与“粮票”结缘,是从读高中时开始的,但对“粮票”的印象大概始于童年。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工农业生产尚不发达,物质极为匮乏。从我懂事起,大人们聚堆聊天时,谈论最多的话题往往是凭票购买生活物资,那时买自行车凭票,穿衣凭布票和棉票,吃饭凭粮票、油票、肉票、蛋票乃至白糖票。到了七十年代初,毛泽东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国民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百姓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得到保障,绝大部分有价“票证”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了人们的生活。然而,“粮票”这一计划经济时代最后的“宠儿”却在中国老百姓手中“吃香”了很多年。别小看这张长不过两寸、宽不到一寸的“有价票证”,它不但关系到人们的吃饭问题,还直接影响着每个公民的身份定位乃至前途命运,其中也包含着我青年时代经历的无数酸甜苦辣。
回想当年,“粮票”可不是任何人都能得到的“免费餐券”,它是持有“粮食供应证”(俗称“粮本”)的城镇人口才有的“特权”,占当时全国人口比例接近90%的农村人是无缘得到的。城镇人口拿到“粮本”有两种选择,一是按照登记的人口定量去国营粮店平价买回粮食,另一种选择是兑换成“粮票”拿到国营餐馆就餐。“粮票”分“全国通用粮票”和“地方粮票”,拿着“全国通用粮票”就可以到国内任何省份的任意一家国营粮店购买平价粮食,或者到全国任何地方的任何“国营餐馆”吃到米面食品。
我出生在农村,自然拿不到城镇户口才有的“粮本”。在我的少年时代,大人们虽然起早贪黑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但是一家人还是填不饱肚子,父母亲非常羡慕在城里吃“公家粮”的亲戚,做梦都想让自己的孩子脱离农村,吃上“公家粮”,端上“公家碗”。这一天终于等来了,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县里一纸录取通知书,让全家人兴奋不已:凡是被县第一中学录取的“优等生”,户口及粮食关系可以转到县城。但《通知书》后面附带一个“条件”,每个学生家庭必须向县粮站上交800斤小麦,粮站方能与学生建立“商品粮”供应关系。可当时正是家中严重缺粮之时,父母、姐姐、嫂子四个劳力全年在生产队里出满勤,全家9口人方能分到2800多斤带皮的粮食,其中大部分是玉米、蚕豆、青稞、谷子(加工小米的原粮)、糜子、荞麦等五谷杂粮,主粮小麦还不到1000斤,就是在这种尴尬条件下,父母亲非常果断,宁愿全家人吃糠咽菜,也不让我错过进城求学的机会。
记得去县城粮站交粮的那天,在队里当干部的父亲破例借来了一辆大木轮的牛板车,找来五只麻袋把家里仅有的两个盛小麦的盏子(盛粮的隔板仓)舀了个底朝天,大清早父子俩啃了块豆面饼喝了碗玉米糊就匆匆忙忙出发了。去往县城的路况极差,总共八、九公里的路程走了两个多小时,前三公里是泥土路,说是“路”,实际上是多年来牛板车在盐碱沼泽中碾压自然形成的两道深深车辙,后大半截是最新铺上厚厚鹅卵石的省道。父亲行走并赶车,因我个头小,只能坐在载满粮食的木板车麻袋顶上。出了村口不远,进入那段名为“胡沟洋”的盐碱沼泽路段,木轮不时深陷在泥水外溢的车辙当中,把那头枣色狸花牛累得又喘粗气又吐白沫,行至名为“贺家板地”的一处灌溉水沟时,由于早前的小桥垮塌失修,别无他路,父亲只好卸下几袋粮食,赶着牛车从沟里硬闯,结果还是车陷沟底牛卧泥潭。
我和父亲挽着裤腿下到泥沟里又抬车又拽牛,幸有过路熟人帮忙,才脱离泥沼,弄得几个人满腿满身都是泥浆,那副狼狈相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到达粮站后,排队过筛、过秤、入仓、开票,又等了三个多小时。出了粮站大门,我俩已经饿得饥肠辘辘,路过县城西街口时,县城里唯有的一家“国营临泽饭店”正在营业,父亲从交粮款中抽出两元让我买点吃的,走进餐馆一打听,小黑板上写有三种食品:“馒头每个二两粮票外加五分钱,包子每个一两粮票外加一角五分钱,猪肉臊子面每碗二两粮票外加三角钱”,闻着服务员端到食客面前的一盘盘美食,我馋得口水直流,当我好不容易挤到收银窗口时,卖票的胖姑娘冷漠地告诉我:“对不起,没有‘粮票’不卖饭!”。没办法,我们只得饿着肚子继续赶路,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们坐在牛板车上默默无语,看着颧骨凸起、脸颊凹进、体格消瘦的父亲,听着板车木轮碾压鹅卵石发出刺耳的“呲呲”声,我内心五味杂陈,暗自下定决心,等我拿到粮本,领到“粮票”,一定要让父亲进城时有饭吃。
在县城读高中期间我住在学校,因为一日三餐大部分缺油水,每月36斤定量粮食根本不够吃,周末回到家中,母亲总是把豆面和玉米面掺到一起,做一些烙饼让我带走,而我也时刻忘不了父亲为我读书交粮那天忍饥挨饿的情景,为让家人出门时身揣“粮票”,我吃饭总是吃个半饱,每学期省出十几斤“粮票”交给父亲,而父母每次都执意不让留下,理由是让我吃饱肚子好长身体。为了细水长流,在校的两年时间里,我积攒了百余斤“粮票”,总想着哪一天家人急需时拿出来。
1978年冬天,我应征入伍,在离家的前几天,我特地赶到县城,凭着一纸《入伍通知书》,把父亲几年来一直不愿接手的“甘肃省地方粮票”统统兑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全国通用粮票”,方才交到父亲手里。但父亲最终也没舍得把这些“粮票”兑换粮食,而是把它保存起来以防万不得已时备用,岂料想,这个“万不得已”再也没有出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首先从中国农村开始,家乡很快推行土地“联产承包到户”责任制,粮食产量连年大幅提高,市场上粮食敞开供应,“粮票”作为计划经济时期若干种有价票证中最后一员退出了历史舞台,当年我交给父亲的那些“粮票”最终又返还到我的手里,变成了收藏品。□牛英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