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子心中的梦与痛
——读郑长春长篇小说《青台镇》有感
刘玉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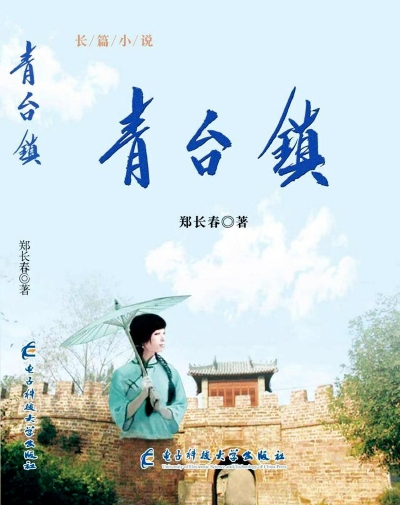
在汇聚着众多文学爱好者的“乡土中原作者群”中,我有幸认识了老家社旗青台(现李店镇)的作家郑长春。为了把青台的历史文化传承下去,他决定趁着年富力强为故乡写一部无愧此生、无愧父老乡亲的“厚重之作”。于是,《青台镇》这部长篇小说应运而生。
小说洋洋洒洒近50万字,在横跨百年的历史长河中,郑长春用成熟的笔法,生动地刻画了张李两个家族的荣辱兴衰,折射出了时代变革和民众命运的跌宕。这些故事内容曲折、思想性强,一个章节就如同一本书,分别选择各种不同的主题和角度,既独立成篇,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独特而丰富的历史镜像。对读者来说,有助于“放宽历史的视界”,将历史从传统的乡镇发展史,延伸到社会史、文化史、战争史、区域史、灾难史、生活史和经济史等方面,并从中发现历史与每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有血有肉的文字里,有亲情、爱情、友情,有义气、侠气和匪气,读罢可以感受到远去的古镇上有多少悲欢离合,变革的年代里有多少荣辱兴衰。
“写作只需遵从内心,不需迎合任何人,只要是内心有感而发,哪怕只言片语,只要认真付诸笔端,就是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作品。”这是郑长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为此,他在叙事结构与语言风格上力求为读者提供独到的审美体验,不管是对历史背景的描述,还是对人性的剖析,都进行了大胆而细致的尝试,甚至将有关社会伦理、地理人文、政经哲学等巧妙地融入其中,使作品具有强烈而鲜明的思想穿透力。
一个作家想写好乡镇、写好农民,只有真正地走进社会底层,深切地了解民众生活才行,否则就不能真正地了解中国,更不可能写出打动人心的作品。郑长春既不同于那些专业作家,也不同于那些业余作家,他应该属于实践型作家,这么多年来,一直做着实际工作,在工作劳动中体验写作的乐趣。实践证明,郑长春对故乡青台是有感情的。他从小生于斯长于斯,虽然后来为了学业离开了这块生他养他的故土,但为了写好这部《青台镇》,他不惜花了整整10年光景,中间多次从西安坐车回青台考察,和镇上老人促膝交谈,了解古镇的前世今生。于是,青台镇的古寨墙,古街两旁的老屋,掉枪河畔的回龙寺、东岳庙、公主坟、登天楼……这些流传着传奇故事的地方,都在小说中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
乡情是游子心中永割不断的牵挂,乡愁是游子笔下最真挚的表达。如今的乡镇,随着社会快速发展而发生巨大变化,许多地方回不去了。回不去的游子,便产生了说不完、道不尽的离愁别绪,随之乡愁文学跟进了,乡愁作品也多了起来。乡土文学多在乡“愁”伤感里,却忽略了情在“新”的进化中,这便是新乡土文学的痛中之“痛”。数千年来,在以寻根文化为主要精神的中国人眼里,乡愁是一种复杂的感情,这感情不同于亲情却又和亲情最有关系,不同于爱情却有走西口时的一步三回首,不同于友情却又总是在每个午夜梦回里想起儿时的玩伴。
“难忘那环绕古镇的掉枪河、围绕镇四周绿树成荫的土寨墙、四个寨门口被时光脚步磨得泛光的青石桥,还有那到处都夹杂着不知是何年何月烧制的碎砖瓦片、散落在灰黑泥土里的锈铜钱……很多的村镇随着时间的流逝变了模样,很多熟悉的人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老去,什么都在变,我们想去寻找从前,可从前只留在记忆里。要想把这记忆永远保存,唯有记录。”这正是郑长春离开故土30多年后为故乡写书立传的初衷。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也是他离开家乡时给母亲留下的铮铮誓言:“有朝一日,我一定要为故乡写一本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书!”
现在,他做到了。可是,有谁知道文字背后的艰辛?有谁能明白一个游子的良苦用心?写作不易,尤其是写长篇小说更是难上加难,每一个篇章都是对作者文字功底、知识储备、生活感受的考验,个中滋味也只有作者本人最清楚。因此,郑长春在小说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表达:“虽然行政区域上的青台镇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作为文学中的《青台镇》却永远活在了我的记忆里。也许,青台镇是不幸的,但它又何其幸矣,因为遇上了我,我懂它的疼……”读到此,实在让人心生酸楚又倍感欣慰。
感谢郑长春用朴实的文字和生动的故事,让我们在一个个落寂的夜晚,从缤纷的梦中听到乡音、看见乡愁、拥抱乡情!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刘玉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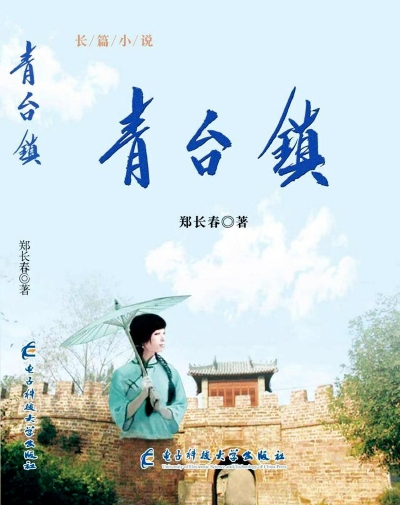
在汇聚着众多文学爱好者的“乡土中原作者群”中,我有幸认识了老家社旗青台(现李店镇)的作家郑长春。为了把青台的历史文化传承下去,他决定趁着年富力强为故乡写一部无愧此生、无愧父老乡亲的“厚重之作”。于是,《青台镇》这部长篇小说应运而生。
小说洋洋洒洒近50万字,在横跨百年的历史长河中,郑长春用成熟的笔法,生动地刻画了张李两个家族的荣辱兴衰,折射出了时代变革和民众命运的跌宕。这些故事内容曲折、思想性强,一个章节就如同一本书,分别选择各种不同的主题和角度,既独立成篇,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独特而丰富的历史镜像。对读者来说,有助于“放宽历史的视界”,将历史从传统的乡镇发展史,延伸到社会史、文化史、战争史、区域史、灾难史、生活史和经济史等方面,并从中发现历史与每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有血有肉的文字里,有亲情、爱情、友情,有义气、侠气和匪气,读罢可以感受到远去的古镇上有多少悲欢离合,变革的年代里有多少荣辱兴衰。
“写作只需遵从内心,不需迎合任何人,只要是内心有感而发,哪怕只言片语,只要认真付诸笔端,就是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作品。”这是郑长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为此,他在叙事结构与语言风格上力求为读者提供独到的审美体验,不管是对历史背景的描述,还是对人性的剖析,都进行了大胆而细致的尝试,甚至将有关社会伦理、地理人文、政经哲学等巧妙地融入其中,使作品具有强烈而鲜明的思想穿透力。
一个作家想写好乡镇、写好农民,只有真正地走进社会底层,深切地了解民众生活才行,否则就不能真正地了解中国,更不可能写出打动人心的作品。郑长春既不同于那些专业作家,也不同于那些业余作家,他应该属于实践型作家,这么多年来,一直做着实际工作,在工作劳动中体验写作的乐趣。实践证明,郑长春对故乡青台是有感情的。他从小生于斯长于斯,虽然后来为了学业离开了这块生他养他的故土,但为了写好这部《青台镇》,他不惜花了整整10年光景,中间多次从西安坐车回青台考察,和镇上老人促膝交谈,了解古镇的前世今生。于是,青台镇的古寨墙,古街两旁的老屋,掉枪河畔的回龙寺、东岳庙、公主坟、登天楼……这些流传着传奇故事的地方,都在小说中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
乡情是游子心中永割不断的牵挂,乡愁是游子笔下最真挚的表达。如今的乡镇,随着社会快速发展而发生巨大变化,许多地方回不去了。回不去的游子,便产生了说不完、道不尽的离愁别绪,随之乡愁文学跟进了,乡愁作品也多了起来。乡土文学多在乡“愁”伤感里,却忽略了情在“新”的进化中,这便是新乡土文学的痛中之“痛”。数千年来,在以寻根文化为主要精神的中国人眼里,乡愁是一种复杂的感情,这感情不同于亲情却又和亲情最有关系,不同于爱情却有走西口时的一步三回首,不同于友情却又总是在每个午夜梦回里想起儿时的玩伴。
“难忘那环绕古镇的掉枪河、围绕镇四周绿树成荫的土寨墙、四个寨门口被时光脚步磨得泛光的青石桥,还有那到处都夹杂着不知是何年何月烧制的碎砖瓦片、散落在灰黑泥土里的锈铜钱……很多的村镇随着时间的流逝变了模样,很多熟悉的人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老去,什么都在变,我们想去寻找从前,可从前只留在记忆里。要想把这记忆永远保存,唯有记录。”这正是郑长春离开故土30多年后为故乡写书立传的初衷。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也是他离开家乡时给母亲留下的铮铮誓言:“有朝一日,我一定要为故乡写一本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书!”
现在,他做到了。可是,有谁知道文字背后的艰辛?有谁能明白一个游子的良苦用心?写作不易,尤其是写长篇小说更是难上加难,每一个篇章都是对作者文字功底、知识储备、生活感受的考验,个中滋味也只有作者本人最清楚。因此,郑长春在小说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表达:“虽然行政区域上的青台镇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作为文学中的《青台镇》却永远活在了我的记忆里。也许,青台镇是不幸的,但它又何其幸矣,因为遇上了我,我懂它的疼……”读到此,实在让人心生酸楚又倍感欣慰。
感谢郑长春用朴实的文字和生动的故事,让我们在一个个落寂的夜晚,从缤纷的梦中听到乡音、看见乡愁、拥抱乡情!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