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社会伤痛 洞察人性幽微
——评刘遥乐长篇小说《噩梦出口》
赵佳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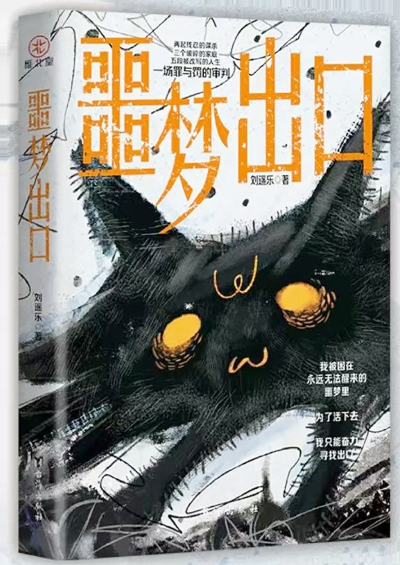
青年作家刘遥乐的长篇小说新作《噩梦出口》(台海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以一起刚刚发生的命案开篇,采用多重叙事视角将另一起尘封多年的案件带入读者视野。在探究真凶的过程中,作者将三个破碎的家庭与五段被改写的人生悲剧尽展笔下,在增强读者撞击感的同时,也启发着读者对未成年人犯罪这一困扰当下的沉痛问题,以及其背后社会、家庭、法律、人性等方面的根源进行深入的拷问与思索。
作品一开始就带给读者突出的紧张感,烂尾楼中出现的被害人指向的是五年前一起劫杀案的凶手吴昭,吴昭当年犯罪时由于未满十四周岁,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最后以矫治教育作为惩治而结案。专案组通过死者吴昭的过往经历以及尸体状态,做出动机推测,并首先锁定犯罪嫌疑人孟玥,即当年劫杀案中死者的女儿。看似即将真相大白,警方却发现孟玥有着近乎“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且雇凶杀人的推测也在调查中被逐步推翻。案情愈发扑朔迷离,悲剧却并未停止。吴昭的母亲陈义红在得知儿子死讯后悲痛欲绝,顺着她的逻辑,在冲动与绝望中选择了持刀报复。当菜刀砍进孟玥的胸腔时,陈义红也被及时赶到的特警击中,最终不治身亡。正当侦破似乎陷入死局时,案情迎来了再次反转。孟玥受伤之后出国的计划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通过步态监测发现此时赶往机场的孟玥竟与案发现场的嫌疑人步态吻合,而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孟玥可能正是其雇佣的替身。
原来孟玥曾休学两年,在这期间寻找到一名与自己样貌身材相当接近的女性,经过微调和训练后代替自己回归现实生活,同时利用公众的思维惯性,引导人们将重返社会后的“孟玥”的异态默认为重大创伤后的应激改变,至此,小说的推理逻辑终于形成闭环。孟玥用这种“颠覆前提”的方式欺骗了警方,读者也沉浸式地掉进了作者精心设计的“圈套”。多层反转的情节设计,不仅增加了作品叙事的紧张感与可读性,还充分彰显了作品中推理逻辑的缜密和贴合自然。
小说将“噩梦”选为作品的题眼,刻画了一系列被噩梦笼罩的悲剧。悬壶济世的精神科主任魏玲因为突如其来的抢劫殒命,而她在自己生命的尽头还在试图规劝少年迷途知返。一场血案引发的连锁反应使许多本来祥和幸福的人生被摧毁,让人唏嘘感叹。
“噩梦”沉痛,作家刘遥乐有意探讨其背后的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家庭教育以及司法预防等诸多沉重问题。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爱的淡漠与匮乏给孩子留下的心灵创伤,甚至使孩子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举止走向情绪化与极端化;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完善、普及也有待提升,这使法治文明推进的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阵痛。在被“噩梦”笼罩时,作品中无论是为母复仇的孟玥,还是为子报仇的陈义红,皆被仇恨与愤怒捆绑,在法律面前选择了一己报复,害人害己终食恶果。这不能不引人深思,当情与法之间产生冲突,罪与罚之间发生分歧,我们该如何选择?作家刘遥乐注重推理逻辑严密、“完美”的同时,尤其突出了对犯罪动机的探究,强化了作品的叙事张力与思想深度。
“噩梦”终究只是梦,而梦的出口处是阳光普照,是新生与安宁。故事的结尾,真凶孟玥受到了法律制裁,而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亦随着社会认识的深化而调整,作品在文学与现实社会中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得“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在作品中得以具象化呈现。无论任何时候,只有坚守法律与道德的底线,以积极的态度看待人生,才有可能驱散阴霾,实现真正意义的自我救赎。
作家刘遥乐将文学作品与社会热点事件结合,用冷静客观的语言与严谨精巧的逻辑叙事,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专注于对社会问题与复杂人性的思考。将现实中残酷的问题,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每个人物都能在现实中找出那个对应的身影。
社会新闻不再是一眼而过,不再是冰冷的受害人与加害者,而是你我心中的每一个疑问,每一次思考,即便永远无法做出完美解答。刘遥乐在重视作品审美属性的同时兼顾社会责任与人文情怀,将作品打造成了一面反映时代与社会现实的多棱镜,最终折射出温暖的人性光芒。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赵佳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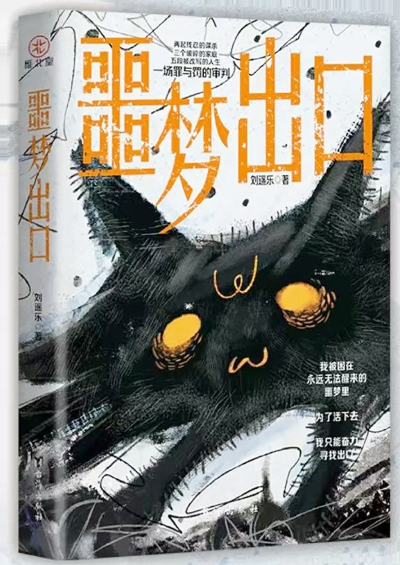
青年作家刘遥乐的长篇小说新作《噩梦出口》(台海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以一起刚刚发生的命案开篇,采用多重叙事视角将另一起尘封多年的案件带入读者视野。在探究真凶的过程中,作者将三个破碎的家庭与五段被改写的人生悲剧尽展笔下,在增强读者撞击感的同时,也启发着读者对未成年人犯罪这一困扰当下的沉痛问题,以及其背后社会、家庭、法律、人性等方面的根源进行深入的拷问与思索。
作品一开始就带给读者突出的紧张感,烂尾楼中出现的被害人指向的是五年前一起劫杀案的凶手吴昭,吴昭当年犯罪时由于未满十四周岁,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最后以矫治教育作为惩治而结案。专案组通过死者吴昭的过往经历以及尸体状态,做出动机推测,并首先锁定犯罪嫌疑人孟玥,即当年劫杀案中死者的女儿。看似即将真相大白,警方却发现孟玥有着近乎“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且雇凶杀人的推测也在调查中被逐步推翻。案情愈发扑朔迷离,悲剧却并未停止。吴昭的母亲陈义红在得知儿子死讯后悲痛欲绝,顺着她的逻辑,在冲动与绝望中选择了持刀报复。当菜刀砍进孟玥的胸腔时,陈义红也被及时赶到的特警击中,最终不治身亡。正当侦破似乎陷入死局时,案情迎来了再次反转。孟玥受伤之后出国的计划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通过步态监测发现此时赶往机场的孟玥竟与案发现场的嫌疑人步态吻合,而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孟玥可能正是其雇佣的替身。
原来孟玥曾休学两年,在这期间寻找到一名与自己样貌身材相当接近的女性,经过微调和训练后代替自己回归现实生活,同时利用公众的思维惯性,引导人们将重返社会后的“孟玥”的异态默认为重大创伤后的应激改变,至此,小说的推理逻辑终于形成闭环。孟玥用这种“颠覆前提”的方式欺骗了警方,读者也沉浸式地掉进了作者精心设计的“圈套”。多层反转的情节设计,不仅增加了作品叙事的紧张感与可读性,还充分彰显了作品中推理逻辑的缜密和贴合自然。
小说将“噩梦”选为作品的题眼,刻画了一系列被噩梦笼罩的悲剧。悬壶济世的精神科主任魏玲因为突如其来的抢劫殒命,而她在自己生命的尽头还在试图规劝少年迷途知返。一场血案引发的连锁反应使许多本来祥和幸福的人生被摧毁,让人唏嘘感叹。
“噩梦”沉痛,作家刘遥乐有意探讨其背后的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家庭教育以及司法预防等诸多沉重问题。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爱的淡漠与匮乏给孩子留下的心灵创伤,甚至使孩子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举止走向情绪化与极端化;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完善、普及也有待提升,这使法治文明推进的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阵痛。在被“噩梦”笼罩时,作品中无论是为母复仇的孟玥,还是为子报仇的陈义红,皆被仇恨与愤怒捆绑,在法律面前选择了一己报复,害人害己终食恶果。这不能不引人深思,当情与法之间产生冲突,罪与罚之间发生分歧,我们该如何选择?作家刘遥乐注重推理逻辑严密、“完美”的同时,尤其突出了对犯罪动机的探究,强化了作品的叙事张力与思想深度。
“噩梦”终究只是梦,而梦的出口处是阳光普照,是新生与安宁。故事的结尾,真凶孟玥受到了法律制裁,而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亦随着社会认识的深化而调整,作品在文学与现实社会中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得“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在作品中得以具象化呈现。无论任何时候,只有坚守法律与道德的底线,以积极的态度看待人生,才有可能驱散阴霾,实现真正意义的自我救赎。
作家刘遥乐将文学作品与社会热点事件结合,用冷静客观的语言与严谨精巧的逻辑叙事,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专注于对社会问题与复杂人性的思考。将现实中残酷的问题,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每个人物都能在现实中找出那个对应的身影。
社会新闻不再是一眼而过,不再是冰冷的受害人与加害者,而是你我心中的每一个疑问,每一次思考,即便永远无法做出完美解答。刘遥乐在重视作品审美属性的同时兼顾社会责任与人文情怀,将作品打造成了一面反映时代与社会现实的多棱镜,最终折射出温暖的人性光芒。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