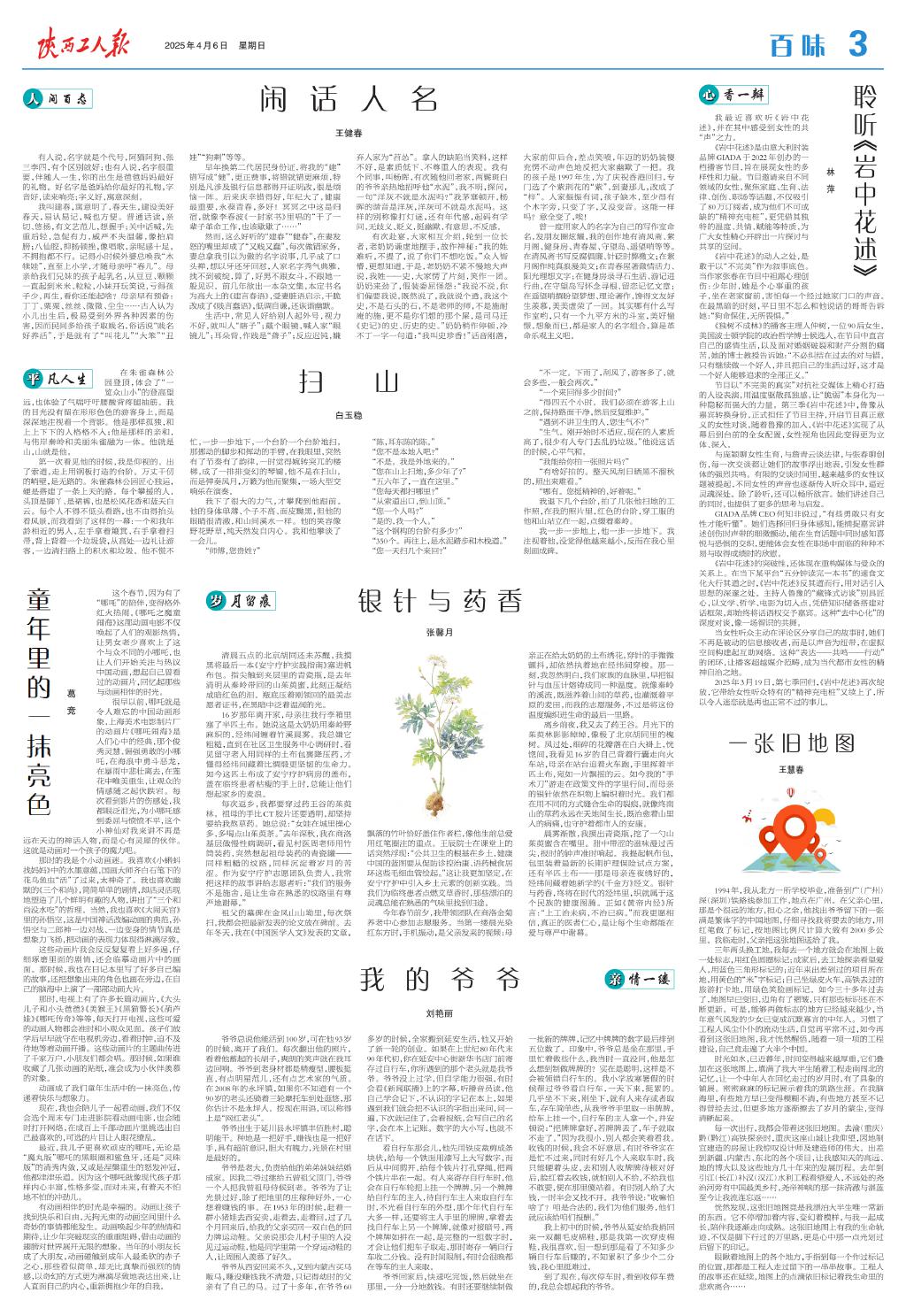扫山
白玉稳
在朱雀森林公园登顶,体会了“一览众山小”的登高望远,也体验了气喘吁吁腰酸背疼腿抽筋。我的目光没有留在形形色色的游客身上,而是深深地注视着一个背影。他是那样孤独,和上上下下的人格格不入;他是那样的亲和,与伟岸秦岭和美丽朱雀融为一体。他就是山,山就是他。
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我是仰视的。出了索道,走上用钢板打造的台阶。万丈千仞的峭壁,是无路的。朱雀森林公园匠心独运,硬是搭建了一条上天的路。每个攀援的人,头顶是脚丫、是裙裤,也是松风花香和蓝天白云。每个人不得不低头看路,也不由得抬头看风景,而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幕:一个和我年龄相近的男人,左手拿着簸箕,右手拿着扫帚,背上背着一个垃圾袋,从高处一边礼让游客,一边清扫路上的积水和垃圾。他不慌不忙,一步一步地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扫,那挪动的脚步和挥动的手臂,在我眼里,突然有了节奏有了韵律,一时觉得婉转突兀的楼梯,成了一排排变幻的琴键,他不是在扫山,而是弹奏风月,万籁为他而聚集,一场大型交响乐在演奏。
我下了很大的力气,才攀爬到他跟前。他的身体单薄、个子不高、面皮黝黑,但他的眼睛很清澈,和山间溪水一样。他的笑容像野花野草,纯天然发自内心。我和他攀谈了一会儿。
“师傅,您贵姓?”
“陈,耳东陈的陈。”
“您不是本地人吧?”
“不是。我是外地来的。”
“您在山上扫地,多少年了?”
“五六年了,一直在这里。”
“您每天都扫哪里?”
“从索道出口,到山顶。”
“您一个人吗?”
“是的,我一个人。”
“这个钢构的台阶有多少?”
“350个。再往上,是水泥踏步和木栈道。”“您一天扫几个来回?”
“不一定。下雨了,刮风了,游客多了,就会多些,一般会两次。”
“一个来回得多少时间?”
“得四五个小时。我们必须在游客上山之前,保持路面干净,然后反复维护。”
“遇到不讲卫生的人,您生气不?”
“生气。刚开始时不适应,现在的人素质高了,很少有人专门去乱扔垃圾。”他说这话的时候,心平气和。
“我能给你拍一张照片吗?”
“有啥好拍的。整天风刮日晒黑不溜秋的,照出来难看。”
“哪有。您挺精神的,好着呢。”
我退下几个台阶,拍了几张他扫地的工作照,在我的照片里,红色的台阶,穿工服的他和山站立在一起,点缀着秦岭。
我一步一步地上,他一步一步地下。我注视着他,没觉得他越来越小,反而在我心里刻画成碑。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白玉稳
在朱雀森林公园登顶,体会了“一览众山小”的登高望远,也体验了气喘吁吁腰酸背疼腿抽筋。我的目光没有留在形形色色的游客身上,而是深深地注视着一个背影。他是那样孤独,和上上下下的人格格不入;他是那样的亲和,与伟岸秦岭和美丽朱雀融为一体。他就是山,山就是他。
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我是仰视的。出了索道,走上用钢板打造的台阶。万丈千仞的峭壁,是无路的。朱雀森林公园匠心独运,硬是搭建了一条上天的路。每个攀援的人,头顶是脚丫、是裙裤,也是松风花香和蓝天白云。每个人不得不低头看路,也不由得抬头看风景,而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幕:一个和我年龄相近的男人,左手拿着簸箕,右手拿着扫帚,背上背着一个垃圾袋,从高处一边礼让游客,一边清扫路上的积水和垃圾。他不慌不忙,一步一步地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扫,那挪动的脚步和挥动的手臂,在我眼里,突然有了节奏有了韵律,一时觉得婉转突兀的楼梯,成了一排排变幻的琴键,他不是在扫山,而是弹奏风月,万籁为他而聚集,一场大型交响乐在演奏。
我下了很大的力气,才攀爬到他跟前。他的身体单薄、个子不高、面皮黝黑,但他的眼睛很清澈,和山间溪水一样。他的笑容像野花野草,纯天然发自内心。我和他攀谈了一会儿。
“师傅,您贵姓?”
“陈,耳东陈的陈。”
“您不是本地人吧?”
“不是。我是外地来的。”
“您在山上扫地,多少年了?”
“五六年了,一直在这里。”
“您每天都扫哪里?”
“从索道出口,到山顶。”
“您一个人吗?”
“是的,我一个人。”
“这个钢构的台阶有多少?”
“350个。再往上,是水泥踏步和木栈道。”“您一天扫几个来回?”
“不一定。下雨了,刮风了,游客多了,就会多些,一般会两次。”
“一个来回得多少时间?”
“得四五个小时。我们必须在游客上山之前,保持路面干净,然后反复维护。”
“遇到不讲卫生的人,您生气不?”
“生气。刚开始时不适应,现在的人素质高了,很少有人专门去乱扔垃圾。”他说这话的时候,心平气和。
“我能给你拍一张照片吗?”
“有啥好拍的。整天风刮日晒黑不溜秋的,照出来难看。”
“哪有。您挺精神的,好着呢。”
我退下几个台阶,拍了几张他扫地的工作照,在我的照片里,红色的台阶,穿工服的他和山站立在一起,点缀着秦岭。
我一步一步地上,他一步一步地下。我注视着他,没觉得他越来越小,反而在我心里刻画成碑。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