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文学“新人”与贾平凹的特别情缘
本报全媒体记者 焦晓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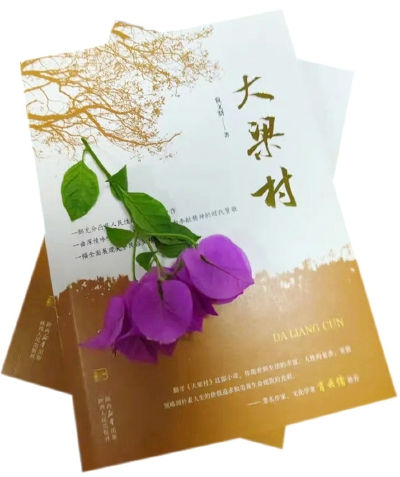
“那确是本好书,让他们多宣传就是!”
这是“五一”前夕,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先生短信回复本报记者采访邀约中的一句话,也是再次对长篇小说《大梁村》作出的评价。事情的缘起还要从去年秋季《大梁村》出版后说起。
2024年9月,陕西省总工会退休干部贠文贤的长篇小说《大梁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耗时两年半创作的作品,以白鹿原上的大梁村为背景,讲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两代人在时代浪潮中的命运沉浮。对于首次出版长篇小说的贠文贤而言,这部作品如同他的“孩子”,既承载着对故土的深情,也寄托着对文学理想的追求。令作者未料想到的是,这部小说为他与素不相识的省作协主席、文坛巨匠贾平凹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
《大梁村》出版后,在读者中和文学评论界引起了良好的反响和评价,也增添了贠文贤对自己作品的自信和底气。当年11月一个普通的午后,贠文贤在书房阅读贾平凹的《古炉》,书中鲜活的人物再次触动了他。忽然间,他想起自己笔下的白鹿原——那片同样饱经沧桑的土地和那里的一个个灵动人物。鬼使神差,他产生了向贾平凹请教的念头。于是,他通过朋友打听到贾平凹的手机号码,便发出了一条短信:“尊敬的贾主席,我是《大梁村》作者贠文贤,为请求您的指导,能否告知您的邮寄地址,以便寄书。”
短信发出后,他自嘲地摇了摇头:“真是异想天开!”然而仅仅隔了一天,他的手机屏幕突然亮起,一条简短回复赫然在目——贾平凹竟发来了邮寄地址。惊喜万分的贠文贤,匆匆忙忙地将书寄出。
书寄出后,贠文贤的心仍是忐忑不安。他深知,贾平凹是著作等身的文学大家,又有公务在身,每日需要处理的事务堆积如山。即便书能送到他手中,是否会被翻开?即便翻开,是否会读下去?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直到12月13日上午,朋友的来电,才为他解开了这些疑问。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位朋友告诉他:“不知啥原因,贾主席没有找到与你交流的短信,正在四处询问你的电话。”原来,他在寄书时,匆忙间忘了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贾平凹多方打听,只为找到这位素未谋面的作者。
当天下午,贠文贤收到贾平凹一条手机短信:“近日读了《大梁村》,我觉得是优秀之作。生活气息极浓,语言朴实但有力。读此书,令我想到很多很多啊。向你祝贺!”过了一个月,2025年1月14日,他又收到了贾平凹的第三条短信:“《大梁村》生活气息浓厚,人物鲜活,年份跨度长,而且是记录了这个时代的好作品,读起来非常有意思,有启示。祝贺你!(平凹)”
短短数十字的两条短信,贠文贤反复读了十余遍,让这位初入文学大门的老人竟然眼眶发热。更令他感动的是,贾平凹不仅认真读完了全书,还主动找寻他的电话号码,只为传达这份鼓励。贠文贤说:“在这次短信交流之前,我和贾主席之间没有任何交集,我们完全是以书为媒介,以文字为桥梁,没有借助任何人的引荐与介绍。”
后来他才知道,贾平凹收到书后,用25天时间认真读完这部40万字的小说。那段时间贾平凹事务很繁忙,但他仍将《大梁村》放在案头,利用乘车、会议间隙的碎片时间阅读。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他看到书中某段情节与某段历史衔接不够紧密时,竟然发现了“被删的部分是个空缺,有些不完整”的瑕疵,将真实感受告诉了作者本人,并发感慨:“读此书,令我想到很多很多!”
在白鹿原文学院的元旦聚会上,文友们围着贠文贤追问了解此事的细节后,有文友感慨:“贾主席的举动,让人看到文学最纯粹的样子。”这种互动交流中,没有利益交换,没有虚与委蛇,只有对文人的本真。白鹿原文学院作家冷丁先生感慨:“贾平凹用行动证明,真正的文学大家,心中自有山河,而非世俗的等级高墙。”
贾平凹与贠文贤的“短信往来”,以书为媒,只看书不问人,对事不对人,而且还不厌其烦地与他这个文学“新人”进行短信往来交流,很快在陕西文坛被传为佳话。本报记者获知此事后,萌生对贾平凹先生进行专访的想法,便委托贠文贤向贾主席转达采访邀请。4月18日下午,贾主席的回复短信道:“你好!我这几天去陕北有重要活动。关于《大梁村》我已谈了我的读后感。记者若写文章,可以用我的那些话。采访就不必了。这望你谅解。那确是本好书,让他们多宣传就是!”
在采访中,贠文贤多次提到“不可思议”与“感动”。对于他而言,这几条短信不仅是对《大梁村》这本书的认可,更对他是一种激励鞭策。贠文贤务过农,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攻读过农学,工作后常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始终情系白鹿原那片故土。《大梁村》出版时,他特意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句话:“谨以此书献给故乡白鹿原”。阅读此书之后,有读者惊叹:原来发生在乡土的那些鸡零狗碎的故事,早已在贠文贤脑海里沉淀成了一部乡村史诗。贾平凹的肯定,让他第一次相信,这些沾着泥土的文字,真的能叩动人心。他说:“至今我与贾老师素未谋面,通过几次短信交流让我明白,文学的价值在于扎根土地、反映时代。”
2025年初春,贠文贤重回家乡大亮村(旧名大梁村)。站在大梁村的旧址上,望着远处绵延的麦田,他忽然理解了贾平凹所说的“想到很多很多。”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那些在土地上坚守的灵魂,因一部小说、几条短信,再次在他的眼前鲜活起来。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本报全媒体记者 焦晓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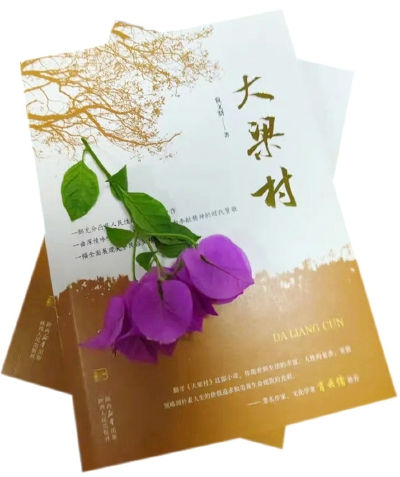
“那确是本好书,让他们多宣传就是!”
这是“五一”前夕,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先生短信回复本报记者采访邀约中的一句话,也是再次对长篇小说《大梁村》作出的评价。事情的缘起还要从去年秋季《大梁村》出版后说起。
2024年9月,陕西省总工会退休干部贠文贤的长篇小说《大梁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耗时两年半创作的作品,以白鹿原上的大梁村为背景,讲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两代人在时代浪潮中的命运沉浮。对于首次出版长篇小说的贠文贤而言,这部作品如同他的“孩子”,既承载着对故土的深情,也寄托着对文学理想的追求。令作者未料想到的是,这部小说为他与素不相识的省作协主席、文坛巨匠贾平凹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
《大梁村》出版后,在读者中和文学评论界引起了良好的反响和评价,也增添了贠文贤对自己作品的自信和底气。当年11月一个普通的午后,贠文贤在书房阅读贾平凹的《古炉》,书中鲜活的人物再次触动了他。忽然间,他想起自己笔下的白鹿原——那片同样饱经沧桑的土地和那里的一个个灵动人物。鬼使神差,他产生了向贾平凹请教的念头。于是,他通过朋友打听到贾平凹的手机号码,便发出了一条短信:“尊敬的贾主席,我是《大梁村》作者贠文贤,为请求您的指导,能否告知您的邮寄地址,以便寄书。”
短信发出后,他自嘲地摇了摇头:“真是异想天开!”然而仅仅隔了一天,他的手机屏幕突然亮起,一条简短回复赫然在目——贾平凹竟发来了邮寄地址。惊喜万分的贠文贤,匆匆忙忙地将书寄出。
书寄出后,贠文贤的心仍是忐忑不安。他深知,贾平凹是著作等身的文学大家,又有公务在身,每日需要处理的事务堆积如山。即便书能送到他手中,是否会被翻开?即便翻开,是否会读下去?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直到12月13日上午,朋友的来电,才为他解开了这些疑问。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位朋友告诉他:“不知啥原因,贾主席没有找到与你交流的短信,正在四处询问你的电话。”原来,他在寄书时,匆忙间忘了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贾平凹多方打听,只为找到这位素未谋面的作者。
当天下午,贠文贤收到贾平凹一条手机短信:“近日读了《大梁村》,我觉得是优秀之作。生活气息极浓,语言朴实但有力。读此书,令我想到很多很多啊。向你祝贺!”过了一个月,2025年1月14日,他又收到了贾平凹的第三条短信:“《大梁村》生活气息浓厚,人物鲜活,年份跨度长,而且是记录了这个时代的好作品,读起来非常有意思,有启示。祝贺你!(平凹)”
短短数十字的两条短信,贠文贤反复读了十余遍,让这位初入文学大门的老人竟然眼眶发热。更令他感动的是,贾平凹不仅认真读完了全书,还主动找寻他的电话号码,只为传达这份鼓励。贠文贤说:“在这次短信交流之前,我和贾主席之间没有任何交集,我们完全是以书为媒介,以文字为桥梁,没有借助任何人的引荐与介绍。”
后来他才知道,贾平凹收到书后,用25天时间认真读完这部40万字的小说。那段时间贾平凹事务很繁忙,但他仍将《大梁村》放在案头,利用乘车、会议间隙的碎片时间阅读。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他看到书中某段情节与某段历史衔接不够紧密时,竟然发现了“被删的部分是个空缺,有些不完整”的瑕疵,将真实感受告诉了作者本人,并发感慨:“读此书,令我想到很多很多!”
在白鹿原文学院的元旦聚会上,文友们围着贠文贤追问了解此事的细节后,有文友感慨:“贾主席的举动,让人看到文学最纯粹的样子。”这种互动交流中,没有利益交换,没有虚与委蛇,只有对文人的本真。白鹿原文学院作家冷丁先生感慨:“贾平凹用行动证明,真正的文学大家,心中自有山河,而非世俗的等级高墙。”
贾平凹与贠文贤的“短信往来”,以书为媒,只看书不问人,对事不对人,而且还不厌其烦地与他这个文学“新人”进行短信往来交流,很快在陕西文坛被传为佳话。本报记者获知此事后,萌生对贾平凹先生进行专访的想法,便委托贠文贤向贾主席转达采访邀请。4月18日下午,贾主席的回复短信道:“你好!我这几天去陕北有重要活动。关于《大梁村》我已谈了我的读后感。记者若写文章,可以用我的那些话。采访就不必了。这望你谅解。那确是本好书,让他们多宣传就是!”
在采访中,贠文贤多次提到“不可思议”与“感动”。对于他而言,这几条短信不仅是对《大梁村》这本书的认可,更对他是一种激励鞭策。贠文贤务过农,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攻读过农学,工作后常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始终情系白鹿原那片故土。《大梁村》出版时,他特意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句话:“谨以此书献给故乡白鹿原”。阅读此书之后,有读者惊叹:原来发生在乡土的那些鸡零狗碎的故事,早已在贠文贤脑海里沉淀成了一部乡村史诗。贾平凹的肯定,让他第一次相信,这些沾着泥土的文字,真的能叩动人心。他说:“至今我与贾老师素未谋面,通过几次短信交流让我明白,文学的价值在于扎根土地、反映时代。”
2025年初春,贠文贤重回家乡大亮村(旧名大梁村)。站在大梁村的旧址上,望着远处绵延的麦田,他忽然理解了贾平凹所说的“想到很多很多。”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那些在土地上坚守的灵魂,因一部小说、几条短信,再次在他的眼前鲜活起来。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