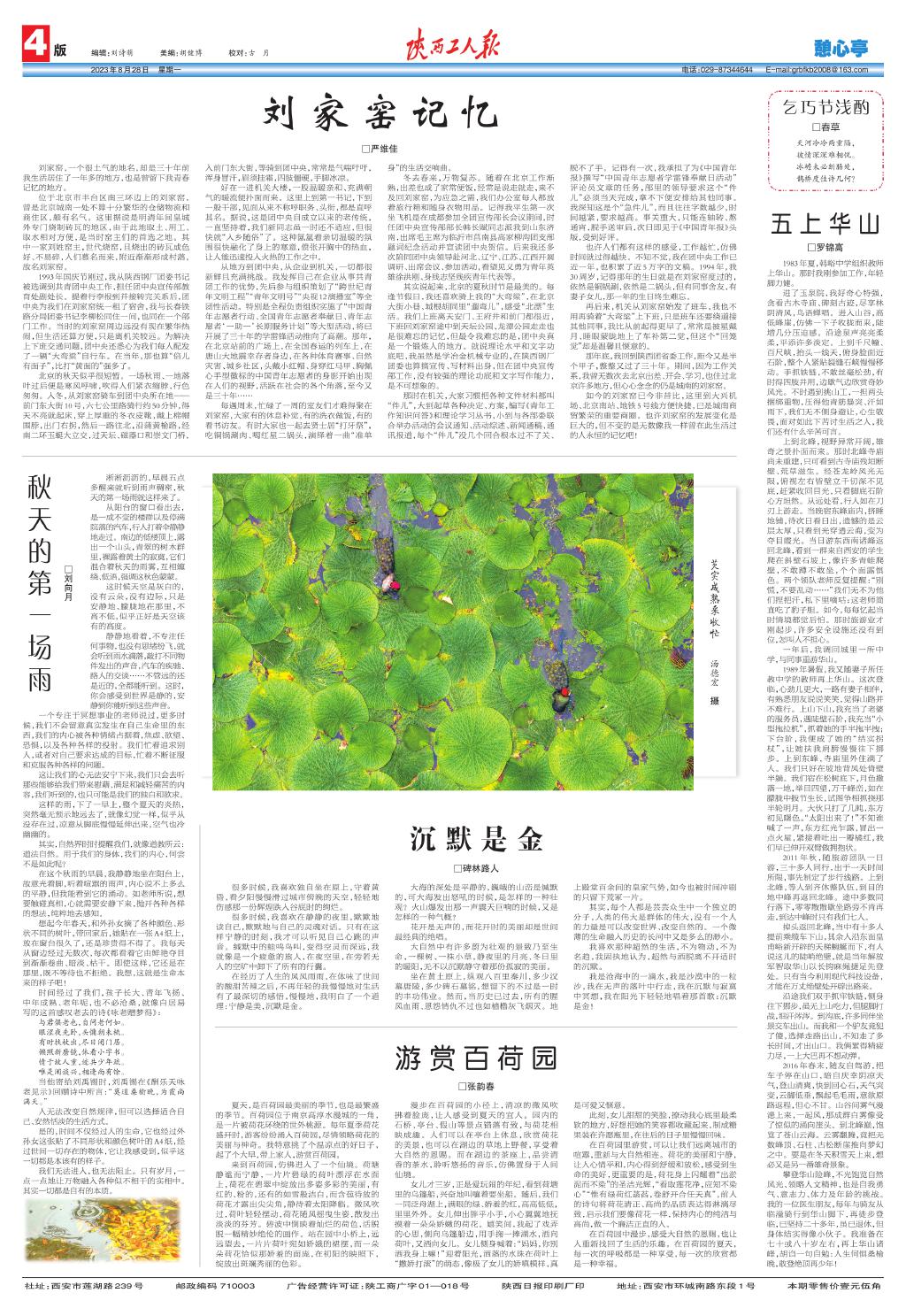刘家窑记忆
□严维佳
刘家窑,一个很土气的地名,却是三十年前我生活居住了一年多的地方,也是曾留下我青春记忆的地方。
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边上的刘家窑,曾是北京城南一处不算十分繁华的仓储物流和商住区,颇有名气。这里据说是明清年间皇城外专门烧制砖瓦的地区,由于此地取土、用工、取水相对方便,是当时窑主们的首选之地。其中一家刘姓窑主,世代烧窑,且烧出的砖瓦成色好、不易碎,人们慕名而来,附近渐渐形成村落,故名刘家窑。
1993年国庆节刚过,我从陕西钢厂团委书记被选调到共青团中央工作,担任团中央宣传部教育处副处长。提着行李报到并接转完关系后,团中央为我们在刘家窑统一租了宿舍,我与长春铁路分局团委书记李柳松同住一间,也同在一个部门工作。当时的刘家窑周边远没有现在繁华热闹,但生活还算方便,只是离机关较远。为解决上下班交通问题,团中央还悉心为我们每人配发了一辆“大弯梁”自行车。在当年,那也算“倍儿有面子”,比打“黄面的”强多了。
北京的秋天似乎很短暂。一场秋雨、一地落叶过后便是寒风呼啸,吹得人们紧衣缩脖,行色匆匆。入冬,从刘家窑骑车到团中央所在地——前门东大街10号,六七公里路骑行约50分钟,得天不亮就起床,穿上厚重的冬衣皮靴,戴上棉帽围脖,出门右拐,然后一路往北,沿蒲黄榆路,经南二环玉蜓大立交,过天坛、磁器口和崇文门桥,入前门东大街,等骑到团中央,常常是气喘吁吁,浑身冒汗,眉须挂霜,四肢僵硬,手脚冰凉。
好在一进机关大楼,一股温暖亲和、充满朝气的暖流便扑面而来。这里上到第一书记,下到一般干部,见面从来不称呼职务、头衔,都是直呼其名。据说,这是团中央自成立以来的老传统,一直坚持着,我们新同志虽一时还不适应,但很快就“入乡随俗”了。这种氤氲着亲切温暖的氛围很快融化了身上的寒意,偾张开胸中的热血,让人能迅速投入火热的工作之中。
从地方到团中央,从企业到机关,一切都很新鲜且充满挑战。我发挥自己在企业从事共青团工作的优势,先后参与组织策划了“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青年文明号”“央视12演播室”等全团性活动。特别是全程负责组织实施了“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全国青年志愿者奉献日、青年志愿者‘一助一’长期服务计划”等大型活动,将已开展了三十年的学雷锋活动推向了高潮。那年,在北京站前的广场上,在全国春运的列车上,在唐山大地震幸存者身边,在各种体育赛事、自然灾害、城乡社区,头戴小红帽、身穿红马甲、胸佩心手型徽标的中国青年志愿者的身影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活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至今又是三十年……
每遇周末,忙碌了一周的室友们才难得聚在刘家窑,大家有的休息补觉,有的洗衣做饭,有的看书访友。有时大家也一起去贤士居“打牙祭”,吃铜锅涮肉、喝红星二锅头,演绎着一曲“准单身”的生活交响曲。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随着在北京工作渐熟,出差也成了家常便饭,经常是说走就走,来不及回刘家窑,为应急之需,我们办公室每人都放着旅行箱和随身衣物用品。记得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是在成都参加全团宣传部长会议期间,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韩长赋同志派我到山东济南,出席毛主席为临沂市莒南县高家柳沟团支部题词纪念活动并宣读团中央贺信。后来我还多次陪同团中央领导赴河北、辽宁、江苏、江西开展调研、出席会议、参加活动,看望见义勇为青年英雄徐洪刚、身残志坚残疾青年代表等。
其实说起来,北京的夏秋时节是最美的。每逢节假日,我还喜欢骑上我的“大弯梁”,在北京大街小巷、城根胡同里“遛弯儿”,感受“北漂”生活。我们上班离天安门、王府井和前门都很近,下班回刘家窑途中到天坛公园、龙潭公园走走也是很难忘的记忆,但最令我难忘的是,团中央真是一个锻炼人的地方。就说理论水平和文字功底吧,我虽然是学冶金机械专业的,在陕西钢厂团委也算搞宣传、写材料出身,但在团中央宣传部工作,没有较强的理论功底和文字写作能力,是不可想象的。
那时在机关,大家习惯把各种文件材料都叫“件儿”,大到起草各种决定、方案,编写《青年工作知识问答》和理论学习丛书,小到与各部委联合举办活动的会议通知、活动综述、新闻通稿、通讯报道,每个“件儿”没几个回合根本过不了关、脱不了手。记得有一次,我承担了为《中国青年报》撰写“中国青年志愿者学雷锋奉献日活动”评论员文章的任务,部里的领导要求这个“件儿”必须当天完成,拿不下便安排给其他同事。我深知这是个“急件儿”,而且往往字数越少,时间越紧,要求越高。事关重大,只能连轴转、熬通宵,脱手送审后,次日即见于《中国青年报》头版,受到好评。
也许人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工作越忙,仿佛时间就过得越快。不知不觉,我在团中央工作已近一年,也积累了近5万字的文稿。1994年,我30周岁,记得那年的生日就是在刘家窑度过的,依然是铜锅涮,依然是二锅头,但有同事舍友,有妻子女儿,那一年的生日终生难忘。
再后来,机关从刘家窑始发了班车,我也不用再骑着“大弯梁”上下班,只是班车还要绕道接其他同事,我比从前起得更早了,常常是披星戴月、睡眼蒙眬地上了车补第二觉,但这个“回笼觉”却是温馨且惬意的。
那年底,我回到陕西团省委工作,距今又是半个甲子,整整又过了三十年。期间,因为工作关系,我曾无数次去北京出差、开会、学习,也住过北京许多地方,但心心念念的仍是城南的刘家窑。
如今的刘家窑已今非昔比,这里到大兴机场、北京南站、地铁5号线方便快捷,已是城南商贸繁荣的重要商圈。也许刘家窑的发展变化是巨大的,但不变的是无数像我一样曾在此生活过的人永恒的记忆吧!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严维佳
刘家窑,一个很土气的地名,却是三十年前我生活居住了一年多的地方,也是曾留下我青春记忆的地方。
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边上的刘家窑,曾是北京城南一处不算十分繁华的仓储物流和商住区,颇有名气。这里据说是明清年间皇城外专门烧制砖瓦的地区,由于此地取土、用工、取水相对方便,是当时窑主们的首选之地。其中一家刘姓窑主,世代烧窑,且烧出的砖瓦成色好、不易碎,人们慕名而来,附近渐渐形成村落,故名刘家窑。
1993年国庆节刚过,我从陕西钢厂团委书记被选调到共青团中央工作,担任团中央宣传部教育处副处长。提着行李报到并接转完关系后,团中央为我们在刘家窑统一租了宿舍,我与长春铁路分局团委书记李柳松同住一间,也同在一个部门工作。当时的刘家窑周边远没有现在繁华热闹,但生活还算方便,只是离机关较远。为解决上下班交通问题,团中央还悉心为我们每人配发了一辆“大弯梁”自行车。在当年,那也算“倍儿有面子”,比打“黄面的”强多了。
北京的秋天似乎很短暂。一场秋雨、一地落叶过后便是寒风呼啸,吹得人们紧衣缩脖,行色匆匆。入冬,从刘家窑骑车到团中央所在地——前门东大街10号,六七公里路骑行约50分钟,得天不亮就起床,穿上厚重的冬衣皮靴,戴上棉帽围脖,出门右拐,然后一路往北,沿蒲黄榆路,经南二环玉蜓大立交,过天坛、磁器口和崇文门桥,入前门东大街,等骑到团中央,常常是气喘吁吁,浑身冒汗,眉须挂霜,四肢僵硬,手脚冰凉。
好在一进机关大楼,一股温暖亲和、充满朝气的暖流便扑面而来。这里上到第一书记,下到一般干部,见面从来不称呼职务、头衔,都是直呼其名。据说,这是团中央自成立以来的老传统,一直坚持着,我们新同志虽一时还不适应,但很快就“入乡随俗”了。这种氤氲着亲切温暖的氛围很快融化了身上的寒意,偾张开胸中的热血,让人能迅速投入火热的工作之中。
从地方到团中央,从企业到机关,一切都很新鲜且充满挑战。我发挥自己在企业从事共青团工作的优势,先后参与组织策划了“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青年文明号”“央视12演播室”等全团性活动。特别是全程负责组织实施了“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全国青年志愿者奉献日、青年志愿者‘一助一’长期服务计划”等大型活动,将已开展了三十年的学雷锋活动推向了高潮。那年,在北京站前的广场上,在全国春运的列车上,在唐山大地震幸存者身边,在各种体育赛事、自然灾害、城乡社区,头戴小红帽、身穿红马甲、胸佩心手型徽标的中国青年志愿者的身影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活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至今又是三十年……
每遇周末,忙碌了一周的室友们才难得聚在刘家窑,大家有的休息补觉,有的洗衣做饭,有的看书访友。有时大家也一起去贤士居“打牙祭”,吃铜锅涮肉、喝红星二锅头,演绎着一曲“准单身”的生活交响曲。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随着在北京工作渐熟,出差也成了家常便饭,经常是说走就走,来不及回刘家窑,为应急之需,我们办公室每人都放着旅行箱和随身衣物用品。记得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是在成都参加全团宣传部长会议期间,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韩长赋同志派我到山东济南,出席毛主席为临沂市莒南县高家柳沟团支部题词纪念活动并宣读团中央贺信。后来我还多次陪同团中央领导赴河北、辽宁、江苏、江西开展调研、出席会议、参加活动,看望见义勇为青年英雄徐洪刚、身残志坚残疾青年代表等。
其实说起来,北京的夏秋时节是最美的。每逢节假日,我还喜欢骑上我的“大弯梁”,在北京大街小巷、城根胡同里“遛弯儿”,感受“北漂”生活。我们上班离天安门、王府井和前门都很近,下班回刘家窑途中到天坛公园、龙潭公园走走也是很难忘的记忆,但最令我难忘的是,团中央真是一个锻炼人的地方。就说理论水平和文字功底吧,我虽然是学冶金机械专业的,在陕西钢厂团委也算搞宣传、写材料出身,但在团中央宣传部工作,没有较强的理论功底和文字写作能力,是不可想象的。
那时在机关,大家习惯把各种文件材料都叫“件儿”,大到起草各种决定、方案,编写《青年工作知识问答》和理论学习丛书,小到与各部委联合举办活动的会议通知、活动综述、新闻通稿、通讯报道,每个“件儿”没几个回合根本过不了关、脱不了手。记得有一次,我承担了为《中国青年报》撰写“中国青年志愿者学雷锋奉献日活动”评论员文章的任务,部里的领导要求这个“件儿”必须当天完成,拿不下便安排给其他同事。我深知这是个“急件儿”,而且往往字数越少,时间越紧,要求越高。事关重大,只能连轴转、熬通宵,脱手送审后,次日即见于《中国青年报》头版,受到好评。
也许人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工作越忙,仿佛时间就过得越快。不知不觉,我在团中央工作已近一年,也积累了近5万字的文稿。1994年,我30周岁,记得那年的生日就是在刘家窑度过的,依然是铜锅涮,依然是二锅头,但有同事舍友,有妻子女儿,那一年的生日终生难忘。
再后来,机关从刘家窑始发了班车,我也不用再骑着“大弯梁”上下班,只是班车还要绕道接其他同事,我比从前起得更早了,常常是披星戴月、睡眼蒙眬地上了车补第二觉,但这个“回笼觉”却是温馨且惬意的。
那年底,我回到陕西团省委工作,距今又是半个甲子,整整又过了三十年。期间,因为工作关系,我曾无数次去北京出差、开会、学习,也住过北京许多地方,但心心念念的仍是城南的刘家窑。
如今的刘家窑已今非昔比,这里到大兴机场、北京南站、地铁5号线方便快捷,已是城南商贸繁荣的重要商圈。也许刘家窑的发展变化是巨大的,但不变的是无数像我一样曾在此生活过的人永恒的记忆吧!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