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其修远兮
——《孤帆觅渡》读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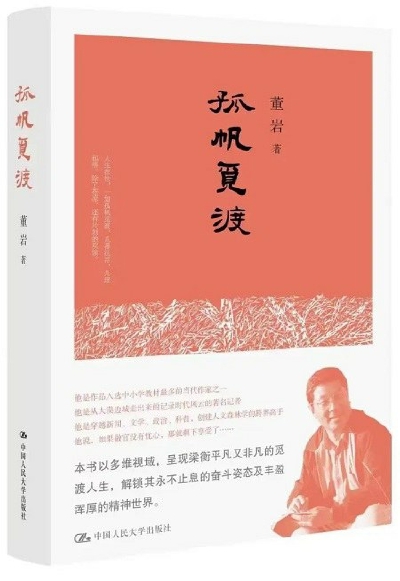
几乎一口气读完董岩所著的《孤帆觅渡》,这是一本集著名记者、作家、官员于一身的梁衡的传记。作者曾是梁衡的博士研究生,对梁衡进行了长久观察、系统采访和追踪研究,可谓写的对象是最熟悉的人。
从作者自序中得知,作者提出写此书时,传主是且信且疑的。不知传主对此书评价如何,笔者以为这是一本写法创新、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生动形象的成功传记。
成功之一是写法创新。本书最大的特点,笔者认为是作者对传记写作方式的创新。人是社会中的人,本书没有拘泥于对传主生平做琐屑的考述,而是在大时代背景的铺陈下,从传主丰富的材料中抽离出来,以“客观叙述+访谈+日记独白”的独特体例,用生动简省的笔墨,将庞杂翔实的第一手素材抽丝剥茧地提炼和多维呈现。通过一个人的故事,展现出时代的发展。它让我们回到并不遥远却又有几分陌生的时代,给我们带来细腻丰富的阅读体验与深刻透辟的人生思考。这既是读者阅读的感受,也是作者创作的初衷。
为写作此书,作者调阅了传主所处时代的有关报纸和文件,摘引了传主所处时代的重大事件,为理解传主的成长成熟过程提供了背景资料。同时,作者对传主进行了多次访谈,阅读了传主数十年的日记,并在书中引用了有关访谈和日记,便于读者知人论世。如《治理整顿与“三刊”工程》一节,记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于1996年12月发出的《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管理的通知》,即“37号文件”。其精神是“控制总量,提高质量,增进效益”。1997年3月,新闻出版署根据“两办”精神下发的报业治理工作的文件,主要目标是针对法制类小报和各种行业报治理3年,计划每年压缩报纸的10%。在中央直接领导下,1997年3月到1998年底,新闻出版署对全国报刊出版共压缩公开报纸300种、公开期刊443种,取消了内部报刊系列,压缩了一批行业报刊,使报刊的绝对数量有了一定程度的减少,基本改变了报刊“散”和“滥”的状况。而具体的操盘手就是传主。
成功之二是真实可信。真实是传记的生命,有的传记过于拔高神话传主,也有的传记丑化歪曲传主。《孤帆觅渡》书名一看就是写一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人生。传主的大半生可谓跌宕起伏,不乏坎坷——大学毕业适逢“文革”爆发,被分配到边疆内蒙古偏僻小县,后来正要提拔,又遭人诬陷,陷入低谷数年。作者并不为名人讳,这些“运交华盖”的经历和心路在书中都有真实记述和描写。其实,作为大半生从事新闻出版的笔者对传主在新闻出版署的工作也曾略有了解,其作品也读过一些,但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比如,笔者也参加过陕西省报业调研并参与调研报告的撰写,但当时对其背景并不太了解,看了该书后才清楚当年传主对报业治理整顿所做的顶层设计和治理举措,其对中国当代报业的有序发展繁荣贡献可谓大焉。
作者除了对梁衡进行了长久观察、系统采访、追踪研究,并将采访研究资料运用到书中外,还阅读并引用了传主的大量文章、日记和访谈,这些一手资料的采用不仅使该书描述丰满,而且增强了全书的真实性。
成功之三是有血有肉。时下,有的人物传记要么流于流水账式的记录,要么无血无肉干巴巴。而这部书将传主形象呈现得很丰满,当然传主的经历本身也很丰富,涉猎面也很广,尤其是中年之后,亦官亦文,社会活动也不少,但该书对传主着墨最多的还是写作,其次是公务,社会活动几乎一笔带过。从第五章标题《文章为重官为轻》既可窥见传主的偏好,也可看出作者对材料的剪裁,对传主而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纸墨之寿,永于金石,是一生为之追求的主要目标,功夫不负有心人,事实上传主开启了散文创作中一个新流派:政治散文。他所倡导的“写大事、大情、大理”与《美文》杂志提倡的“大散文”观点一脉相承,极大地推动了当代中国散文的繁荣。
2004年,梁衡在他主编的大学生文化读本《爱国的理由》中写道:“爱国,永远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存在的支柱,也是做人的起码标准。”只有能触发国家、民族和全体民众共有情感的大情大理,才是文学的灵魂。在何西来看来,梁衡是做领导工作的,他规范别人的东西也首先规范了他自己。要别人守规矩,自己就得先做到。这就是说,在创作中,很少“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那样的浪漫。他的作品,无不体现他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意识。他的作品,是在规矩之内的创作,居然达到了某种看不出、本不太看得出规矩的境地,人们就不能不佩服他的才力和本事。他能做到超越,创新而不逾矩。
正如蒋巍所言,梁衡文章的最动人之处,在于字里行间对人民的绵长深情。“无论什么人走到他的笔下,他都拿人民的感情、人民的评判作标尺,他都以老百姓的目光来审视。我之所以被感动并且钦敬,是因为梁衡的这种视角和价值判断是真诚而非矫饰的,是本色而非做作的,是一以贯之而非偶然一见的。他坚守着自己的百姓本色。”
梁衡认为,写作是社会化的工作,满意不满意应当由社会、读者来检验、评判。作家的作品不是私有的,而是社会的结晶、时代的产物;他的创作不是纯粹为了宣泄个人化的情绪,而是面向大众的社会化写作。只有站在政治的高度,胸怀忧国忧民之心,摆脱针眼窥天、无病呻吟、自我陶醉的私人化写作,这样的文章才有力度和厚度,才能达到治国的高度,成为经典。
成功之四是形象生动。笔者虽在省级新闻出版单位和机关供职大半辈子,但与传主无交集,印象传主是威严的领导,是顶头上司的上司。因此读该书之初还有点畏难情绪,不知是否能读下去。不料一读而不可收拾,几天来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手不释卷,这与作者生动的文笔和形象的描述密不可分。比如在《新闻与文学》一节中写道:“单一品种的树林并不一定好,不同树种长在一起的混交林,可以合理利用土壤养分,减少病虫害,长得更茂盛。”这使笔者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初,陕西作家成立“群木文学社”,互相学习、互相竞争,最终长成文学大树。又如梁晓声认为,“政治散文”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有过,但也很难称其为散文。故这一文本,后来差不多成了中国文苑的一处荒圃。梁衡的“政治散文”,使那荒圃有了灿然绽放的花朵。
此外,该书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官员写作是提升素质、有益工作、利国利民的好事。传主表示,其实这之间并不矛盾,当官是一个制高点,在这个平台上,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政务,这些工作一方面提供了鲜活的、只有在这个高级层面上才能获得的素材;另一方面锻炼了敏锐的思维,丰富的政治阅历和思想高度对于文学创作和研究都是难得的条件。当官的不利因素就是公务繁忙、时间有限。我曾说过,我要编织一张细密的网,把时间之鱼网住,不让它溜走。我的许多文章都是在会议间隙、在旅途中一点点构思出来的,再见缝插针地写下来,最后反复打磨推敲。这么多年来,我在新闻这个行当里揉来揉去,在写作上反复实践,在管理上反复实践,最后悟出了一些道理。其实,不管是做官,还是写作、研究,最后都要归结到一个“理”字,这是它们的相通之处。笔者以为此处的“理”,当指真理。
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冯牧赞同“仕而优则文”,认为梁衡沿袭了两三千年来中国的散文传统,难能可贵。他的散文写得很好,又是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仕而优则文”,这对文学创作和管理工作都是好事。
记得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也说过:一个人能够写一手好文章,这是一个人的美德。你日后无论从事何种工作,从军也好,从政也好,从工从商也好,都得有一个基本的本领,就是写作的本领。或如笔者的大学同窗、长江学者李浩在《文学与高尔夫》一文中的高论:“作为业余的休闲项目,文学写作无论如何要比打麻将、泡歌厅更高雅,比钓鱼、打太极拳含更多智力保健意味,比高尔夫、攀岩更节俭。”当然,“有人讥讽其为附庸风雅,但附庸这样的风雅远比附庸腐朽文化高明。从这个意义上说,附庸风雅也就是附庸先进文化,这样的附庸和追求应理直气壮地倡导,应使其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气。”而且“公务员们读文学、写文学,所以他们也懂得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对专业作家和艺术家提出的要求建议,能更好地听取采纳,对作家创作所需经费及条件,也能积极给予解决。为了鼓励专业作家深入生活,陕西有作家在县市及企业挂职的制度。有时公务员不光是写作爱好者,而且还能成为真正文学艺术的赞助人,为作家艺术家的工作生活解决许多实际问题。”诚哉斯言!梁衡的为人为文也证明了这一点。□王新民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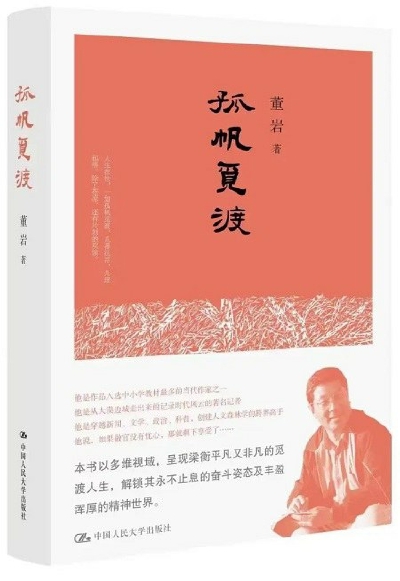
几乎一口气读完董岩所著的《孤帆觅渡》,这是一本集著名记者、作家、官员于一身的梁衡的传记。作者曾是梁衡的博士研究生,对梁衡进行了长久观察、系统采访和追踪研究,可谓写的对象是最熟悉的人。
从作者自序中得知,作者提出写此书时,传主是且信且疑的。不知传主对此书评价如何,笔者以为这是一本写法创新、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生动形象的成功传记。
成功之一是写法创新。本书最大的特点,笔者认为是作者对传记写作方式的创新。人是社会中的人,本书没有拘泥于对传主生平做琐屑的考述,而是在大时代背景的铺陈下,从传主丰富的材料中抽离出来,以“客观叙述+访谈+日记独白”的独特体例,用生动简省的笔墨,将庞杂翔实的第一手素材抽丝剥茧地提炼和多维呈现。通过一个人的故事,展现出时代的发展。它让我们回到并不遥远却又有几分陌生的时代,给我们带来细腻丰富的阅读体验与深刻透辟的人生思考。这既是读者阅读的感受,也是作者创作的初衷。
为写作此书,作者调阅了传主所处时代的有关报纸和文件,摘引了传主所处时代的重大事件,为理解传主的成长成熟过程提供了背景资料。同时,作者对传主进行了多次访谈,阅读了传主数十年的日记,并在书中引用了有关访谈和日记,便于读者知人论世。如《治理整顿与“三刊”工程》一节,记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于1996年12月发出的《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管理的通知》,即“37号文件”。其精神是“控制总量,提高质量,增进效益”。1997年3月,新闻出版署根据“两办”精神下发的报业治理工作的文件,主要目标是针对法制类小报和各种行业报治理3年,计划每年压缩报纸的10%。在中央直接领导下,1997年3月到1998年底,新闻出版署对全国报刊出版共压缩公开报纸300种、公开期刊443种,取消了内部报刊系列,压缩了一批行业报刊,使报刊的绝对数量有了一定程度的减少,基本改变了报刊“散”和“滥”的状况。而具体的操盘手就是传主。
成功之二是真实可信。真实是传记的生命,有的传记过于拔高神话传主,也有的传记丑化歪曲传主。《孤帆觅渡》书名一看就是写一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人生。传主的大半生可谓跌宕起伏,不乏坎坷——大学毕业适逢“文革”爆发,被分配到边疆内蒙古偏僻小县,后来正要提拔,又遭人诬陷,陷入低谷数年。作者并不为名人讳,这些“运交华盖”的经历和心路在书中都有真实记述和描写。其实,作为大半生从事新闻出版的笔者对传主在新闻出版署的工作也曾略有了解,其作品也读过一些,但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比如,笔者也参加过陕西省报业调研并参与调研报告的撰写,但当时对其背景并不太了解,看了该书后才清楚当年传主对报业治理整顿所做的顶层设计和治理举措,其对中国当代报业的有序发展繁荣贡献可谓大焉。
作者除了对梁衡进行了长久观察、系统采访、追踪研究,并将采访研究资料运用到书中外,还阅读并引用了传主的大量文章、日记和访谈,这些一手资料的采用不仅使该书描述丰满,而且增强了全书的真实性。
成功之三是有血有肉。时下,有的人物传记要么流于流水账式的记录,要么无血无肉干巴巴。而这部书将传主形象呈现得很丰满,当然传主的经历本身也很丰富,涉猎面也很广,尤其是中年之后,亦官亦文,社会活动也不少,但该书对传主着墨最多的还是写作,其次是公务,社会活动几乎一笔带过。从第五章标题《文章为重官为轻》既可窥见传主的偏好,也可看出作者对材料的剪裁,对传主而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纸墨之寿,永于金石,是一生为之追求的主要目标,功夫不负有心人,事实上传主开启了散文创作中一个新流派:政治散文。他所倡导的“写大事、大情、大理”与《美文》杂志提倡的“大散文”观点一脉相承,极大地推动了当代中国散文的繁荣。
2004年,梁衡在他主编的大学生文化读本《爱国的理由》中写道:“爱国,永远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存在的支柱,也是做人的起码标准。”只有能触发国家、民族和全体民众共有情感的大情大理,才是文学的灵魂。在何西来看来,梁衡是做领导工作的,他规范别人的东西也首先规范了他自己。要别人守规矩,自己就得先做到。这就是说,在创作中,很少“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那样的浪漫。他的作品,无不体现他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意识。他的作品,是在规矩之内的创作,居然达到了某种看不出、本不太看得出规矩的境地,人们就不能不佩服他的才力和本事。他能做到超越,创新而不逾矩。
正如蒋巍所言,梁衡文章的最动人之处,在于字里行间对人民的绵长深情。“无论什么人走到他的笔下,他都拿人民的感情、人民的评判作标尺,他都以老百姓的目光来审视。我之所以被感动并且钦敬,是因为梁衡的这种视角和价值判断是真诚而非矫饰的,是本色而非做作的,是一以贯之而非偶然一见的。他坚守着自己的百姓本色。”
梁衡认为,写作是社会化的工作,满意不满意应当由社会、读者来检验、评判。作家的作品不是私有的,而是社会的结晶、时代的产物;他的创作不是纯粹为了宣泄个人化的情绪,而是面向大众的社会化写作。只有站在政治的高度,胸怀忧国忧民之心,摆脱针眼窥天、无病呻吟、自我陶醉的私人化写作,这样的文章才有力度和厚度,才能达到治国的高度,成为经典。
成功之四是形象生动。笔者虽在省级新闻出版单位和机关供职大半辈子,但与传主无交集,印象传主是威严的领导,是顶头上司的上司。因此读该书之初还有点畏难情绪,不知是否能读下去。不料一读而不可收拾,几天来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手不释卷,这与作者生动的文笔和形象的描述密不可分。比如在《新闻与文学》一节中写道:“单一品种的树林并不一定好,不同树种长在一起的混交林,可以合理利用土壤养分,减少病虫害,长得更茂盛。”这使笔者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初,陕西作家成立“群木文学社”,互相学习、互相竞争,最终长成文学大树。又如梁晓声认为,“政治散文”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有过,但也很难称其为散文。故这一文本,后来差不多成了中国文苑的一处荒圃。梁衡的“政治散文”,使那荒圃有了灿然绽放的花朵。
此外,该书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官员写作是提升素质、有益工作、利国利民的好事。传主表示,其实这之间并不矛盾,当官是一个制高点,在这个平台上,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政务,这些工作一方面提供了鲜活的、只有在这个高级层面上才能获得的素材;另一方面锻炼了敏锐的思维,丰富的政治阅历和思想高度对于文学创作和研究都是难得的条件。当官的不利因素就是公务繁忙、时间有限。我曾说过,我要编织一张细密的网,把时间之鱼网住,不让它溜走。我的许多文章都是在会议间隙、在旅途中一点点构思出来的,再见缝插针地写下来,最后反复打磨推敲。这么多年来,我在新闻这个行当里揉来揉去,在写作上反复实践,在管理上反复实践,最后悟出了一些道理。其实,不管是做官,还是写作、研究,最后都要归结到一个“理”字,这是它们的相通之处。笔者以为此处的“理”,当指真理。
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冯牧赞同“仕而优则文”,认为梁衡沿袭了两三千年来中国的散文传统,难能可贵。他的散文写得很好,又是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仕而优则文”,这对文学创作和管理工作都是好事。
记得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也说过:一个人能够写一手好文章,这是一个人的美德。你日后无论从事何种工作,从军也好,从政也好,从工从商也好,都得有一个基本的本领,就是写作的本领。或如笔者的大学同窗、长江学者李浩在《文学与高尔夫》一文中的高论:“作为业余的休闲项目,文学写作无论如何要比打麻将、泡歌厅更高雅,比钓鱼、打太极拳含更多智力保健意味,比高尔夫、攀岩更节俭。”当然,“有人讥讽其为附庸风雅,但附庸这样的风雅远比附庸腐朽文化高明。从这个意义上说,附庸风雅也就是附庸先进文化,这样的附庸和追求应理直气壮地倡导,应使其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气。”而且“公务员们读文学、写文学,所以他们也懂得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对专业作家和艺术家提出的要求建议,能更好地听取采纳,对作家创作所需经费及条件,也能积极给予解决。为了鼓励专业作家深入生活,陕西有作家在县市及企业挂职的制度。有时公务员不光是写作爱好者,而且还能成为真正文学艺术的赞助人,为作家艺术家的工作生活解决许多实际问题。”诚哉斯言!梁衡的为人为文也证明了这一点。□王新民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