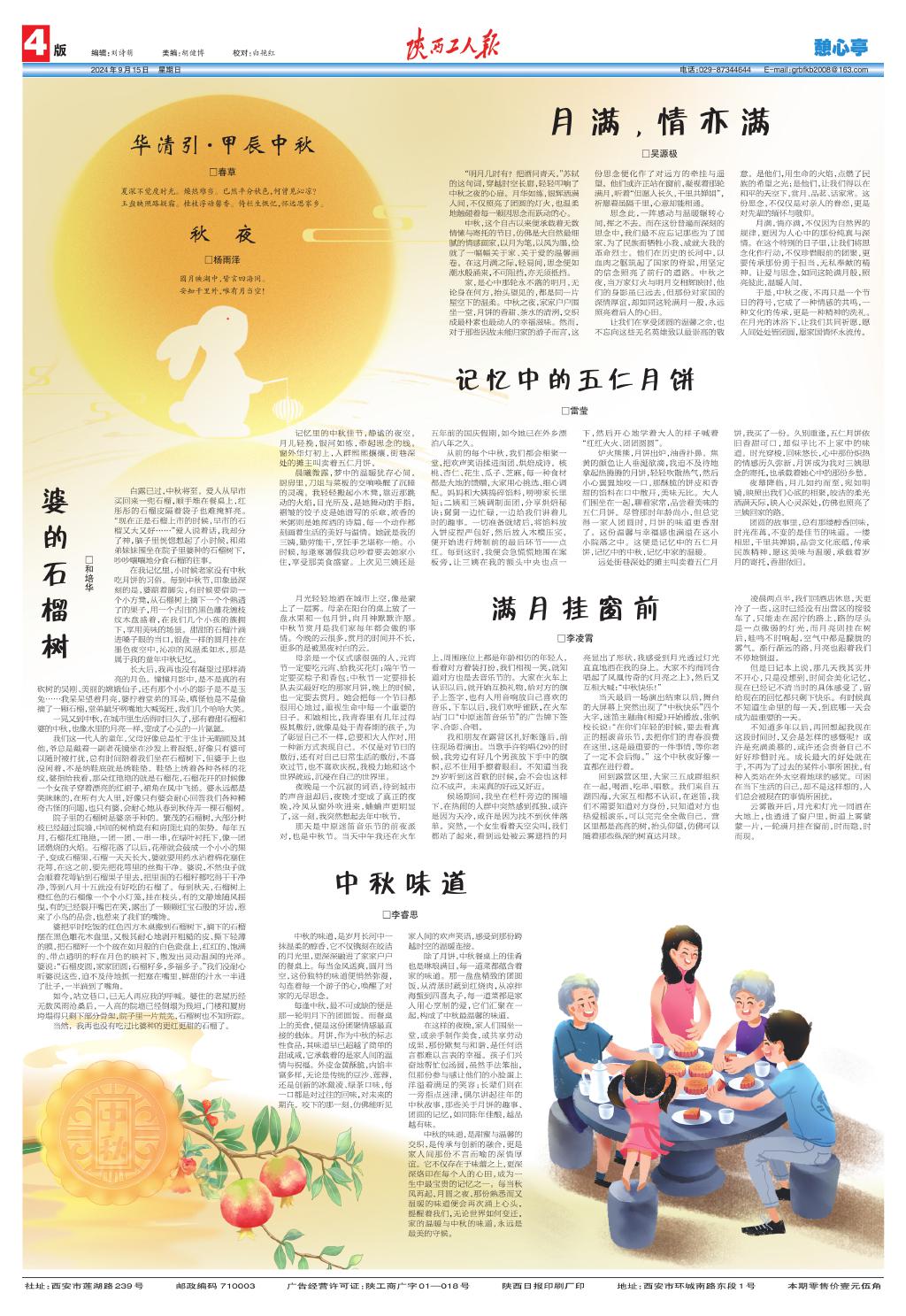婆的石榴树
□和培华
白露已过,中秋将至。爱人从早市买回来一兜石榴,顺手堆在餐桌上,红彤彤的石榴皮隔着袋子也难掩鲜亮。“现在正是石榴上市的时候,早市的石榴又大又好……”爱人说着话,我却分了神,脑子里恍惚想起了小时候,和弟弟妹妹围坐在院子里婆种的石榴树下,吵吵嚷嚷地分食石榴的往事。
在我记忆里,小时候老家没有中秋吃月饼的习俗。每到中秋节,印象最深刻的是,婆踮着脚尖,有时候要借助一个小方凳,从石榴树上摘下一个个熟透了的果子,用一个古旧的黑色雕花缠枝纹木盘盛着,在我们几个小孩的簇拥下,享用美味的场景。甜甜的石榴汁淌进嗓子眼的当口,银盘一样的圆月挂在墨色夜空中,沁凉的风温柔如水,那是属于我的童年中秋记忆。
长大后,我再也没有凝望过那样清亮的月色。憧憧月影中,是不是真的有砍树的吴刚、美丽的嫦娥仙子,还有那个小小的影子是不是玉兔……我呆呆望着月亮,婆拧着堂弟的耳朵,嗔怪他是不是偷摘了一颗石榴,堂弟龇牙咧嘴地大喊冤枉,我们几个哈哈大笑。
一晃又到中秋,在城市里生活得时日久了,那有着甜石榴和婆的中秋,也像水里的月亮一样,变成了心头的一片氤氲。
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父母好像总是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其他,爷总是戴着一副老花镜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好像只有婆可以随时被打扰,总有时间陪着我们坐在石榴树下,但婆手上也没闲着,不是纳鞋底就是绣鞋垫。鞋垫上绣着各种各样的花纹,婆指给我看,那朵红艳艳的就是石榴花,石榴花开的时候像一个女孩子穿着漂亮的红裙子,裙角在风中飞扬。婆永远都是笑眯眯的,在所有大人里,好像只有婆会耐心回答我们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也只有婆,会耐心地从春到秋侍弄一棵石榴树。
院子里的石榴树是婆亲手种的。繁茂的石榴树,大部分树枝已经超过院墙,中间的树梢竟有和房顶比肩的架势。每年五月,石榴花红艳艳,一团一团、一串一串,在绿叶衬托下,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石榴花落了以后,花蒂就会鼓成一个小小的果子,变成石榴果,石榴一天天长大,婆就要用药水沾着棉花塞住花萼,在这之前,要先把花萼里的丝掏干净。婆说,不然虫子就会顺着花萼钻到石榴果子里去,把里面的石榴籽都吃得干干净净,等到八月十五就没有好吃的石榴了。每到秋天,石榴树上橙红色的石榴像一个个小灯笼,挂在枝头,有的文静地随风摇曳,有的已经裂开嘴巴在笑,露出了一颗颗红宝石般的牙齿,惹来了小鸟的品尝,也惹来了我们的嘴馋。
婆把平时吃饭的红色四方木桌搬到石榴树下,摘下的石榴摆在黑色雕花木盘里,又极其耐心地剥开粗糙的皮、撕下轻薄的膜,把石榴籽一个个放在如月般的白色瓷盘上,红红的、饱满的、带点透明的籽在月色的映衬下,散发出灵动温润的光泽。婆说:“石榴皮圆,家家团圆;石榴籽多,多福多子。”我们没耐心听婆说这些,迫不及待地抓一把塞在嘴里,鲜甜的汁水一半进了肚子,一半淌到了嘴角。
如今,站立巷口,已无人再应我的呼喊。婆住的老屋历经无数风雨沧桑后,一人高的院墙已经倒塌为残垣,门楼和厦房垮塌得只剩下部分骨架,院子里一片荒芜,石榴树也不知所踪。
当然,我再也没有吃过比婆种的更红更甜的石榴了。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和培华
白露已过,中秋将至。爱人从早市买回来一兜石榴,顺手堆在餐桌上,红彤彤的石榴皮隔着袋子也难掩鲜亮。“现在正是石榴上市的时候,早市的石榴又大又好……”爱人说着话,我却分了神,脑子里恍惚想起了小时候,和弟弟妹妹围坐在院子里婆种的石榴树下,吵吵嚷嚷地分食石榴的往事。
在我记忆里,小时候老家没有中秋吃月饼的习俗。每到中秋节,印象最深刻的是,婆踮着脚尖,有时候要借助一个小方凳,从石榴树上摘下一个个熟透了的果子,用一个古旧的黑色雕花缠枝纹木盘盛着,在我们几个小孩的簇拥下,享用美味的场景。甜甜的石榴汁淌进嗓子眼的当口,银盘一样的圆月挂在墨色夜空中,沁凉的风温柔如水,那是属于我的童年中秋记忆。
长大后,我再也没有凝望过那样清亮的月色。憧憧月影中,是不是真的有砍树的吴刚、美丽的嫦娥仙子,还有那个小小的影子是不是玉兔……我呆呆望着月亮,婆拧着堂弟的耳朵,嗔怪他是不是偷摘了一颗石榴,堂弟龇牙咧嘴地大喊冤枉,我们几个哈哈大笑。
一晃又到中秋,在城市里生活得时日久了,那有着甜石榴和婆的中秋,也像水里的月亮一样,变成了心头的一片氤氲。
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父母好像总是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其他,爷总是戴着一副老花镜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好像只有婆可以随时被打扰,总有时间陪着我们坐在石榴树下,但婆手上也没闲着,不是纳鞋底就是绣鞋垫。鞋垫上绣着各种各样的花纹,婆指给我看,那朵红艳艳的就是石榴花,石榴花开的时候像一个女孩子穿着漂亮的红裙子,裙角在风中飞扬。婆永远都是笑眯眯的,在所有大人里,好像只有婆会耐心回答我们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也只有婆,会耐心地从春到秋侍弄一棵石榴树。
院子里的石榴树是婆亲手种的。繁茂的石榴树,大部分树枝已经超过院墙,中间的树梢竟有和房顶比肩的架势。每年五月,石榴花红艳艳,一团一团、一串一串,在绿叶衬托下,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石榴花落了以后,花蒂就会鼓成一个小小的果子,变成石榴果,石榴一天天长大,婆就要用药水沾着棉花塞住花萼,在这之前,要先把花萼里的丝掏干净。婆说,不然虫子就会顺着花萼钻到石榴果子里去,把里面的石榴籽都吃得干干净净,等到八月十五就没有好吃的石榴了。每到秋天,石榴树上橙红色的石榴像一个个小灯笼,挂在枝头,有的文静地随风摇曳,有的已经裂开嘴巴在笑,露出了一颗颗红宝石般的牙齿,惹来了小鸟的品尝,也惹来了我们的嘴馋。
婆把平时吃饭的红色四方木桌搬到石榴树下,摘下的石榴摆在黑色雕花木盘里,又极其耐心地剥开粗糙的皮、撕下轻薄的膜,把石榴籽一个个放在如月般的白色瓷盘上,红红的、饱满的、带点透明的籽在月色的映衬下,散发出灵动温润的光泽。婆说:“石榴皮圆,家家团圆;石榴籽多,多福多子。”我们没耐心听婆说这些,迫不及待地抓一把塞在嘴里,鲜甜的汁水一半进了肚子,一半淌到了嘴角。
如今,站立巷口,已无人再应我的呼喊。婆住的老屋历经无数风雨沧桑后,一人高的院墙已经倒塌为残垣,门楼和厦房垮塌得只剩下部分骨架,院子里一片荒芜,石榴树也不知所踪。
当然,我再也没有吃过比婆种的更红更甜的石榴了。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