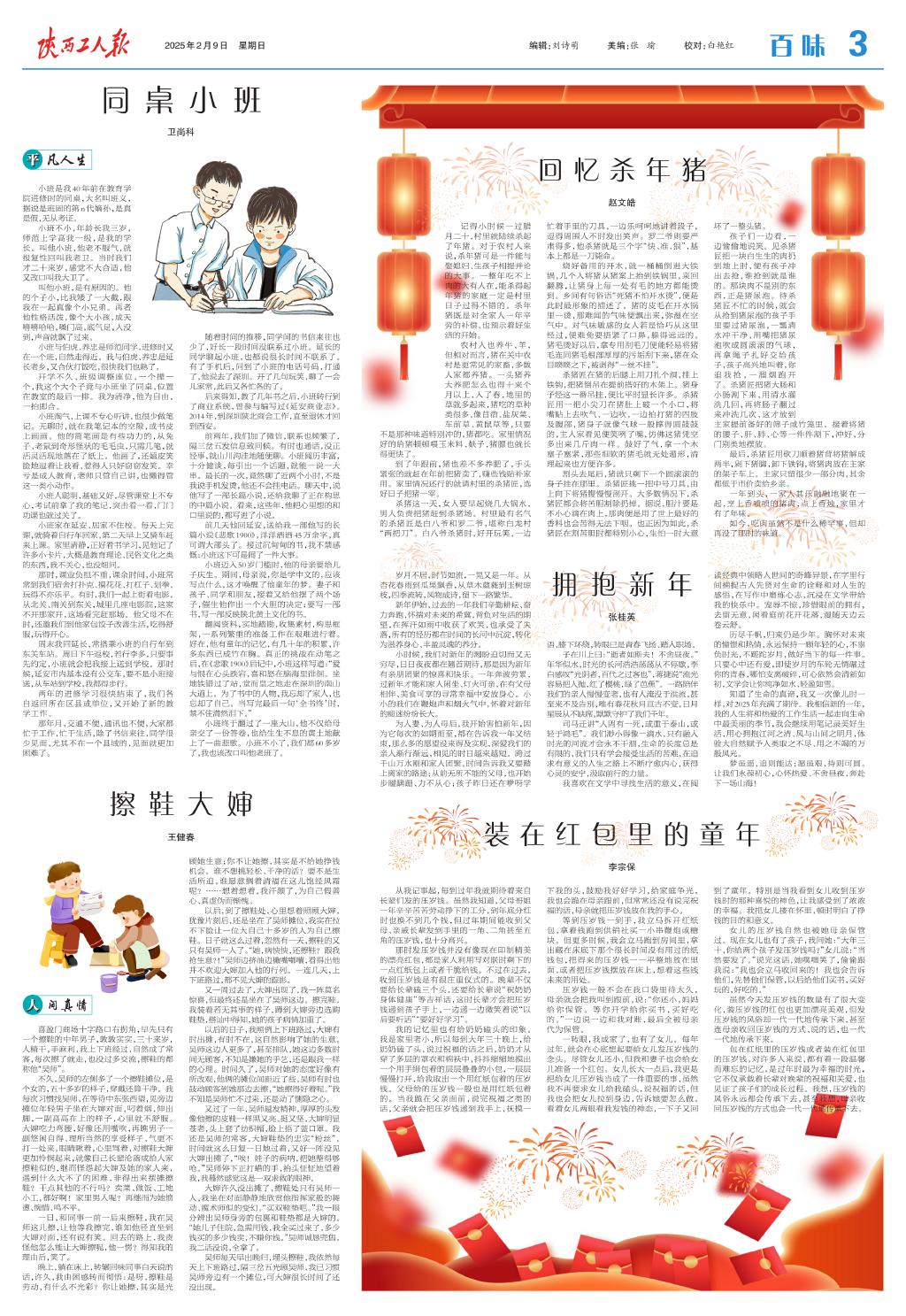擦鞋大婶
王健春

喜盈门商场十字路口右拐角,早先只有一个擦鞋的中年男子,敦敦实实,三十来岁,人精干,手麻利,我上下班经过,自然成了常客,每次擦了就走,也没过多交流,擦鞋的都称他“吴师”。
不久,吴师的左侧多了一个擦鞋摊位,是个女的,五十多岁的样子,穿戴还算干净。我每次习惯找吴师,在等待中东张西望,见旁边摊位年轻男子坐在大婶对面,叼着烟,伸出脚,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心里就不舒服。大婶吃力弯腰,好像还用嘴吹,再瞧男子一副悠闲自得、理所当然的享受样子,气更不打一处来,眼睛瞅着,心里骂着,对擦鞋大婶更加怜悯起来,就像自己长辈沦落成给人家擦鞋似的,继而怪怨起大婶及她的家人来,遇到什么大不了的困难,非得出来摆摊擦鞋?干点其他的不行吗?卖菜、做饭、工地小工,都好啊!家里男人呢?再继而为她愤懑、惋惜、鸣不平。
一日,和同事一前一后来擦鞋,我在吴师这儿擦,让他等我擦完,谁知他径直坐到大婶对面,还有说有笑。回去的路上,我责怪他怎么能让大婶擦呢,他一愣?得知我的理由后,笑了。
晚上,躺在床上,转辗回味同事白天说的话,许久,我由困惑转而彻悟:是呀,擦鞋是劳动,有什么不光彩?你让她擦,其实是光顾她生意;你不让她擦,其实是不给她挣钱机会。谁不想挑轻松、干净的活?要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搁着清福在这儿饱经风霜呢?……想着想着,我汗颜了,为自己假善心、真虚伪而惭愧。
以后,到了擦鞋处,心里想着照顾大婶,犹豫片刻后,还是坐在了吴师摊位,我实在拉不下脸让一位大自己十多岁的人为自己擦鞋。日子就这么过着,忽然有一天,擦鞋的又只有吴师一人了。“她,病怏怏,还擦鞋?跟我抢生意?!”吴师边挤油边撇嘴嘟囔,看得出他并不欢迎大婶加入他的行列。一连几天,上下班路过,都不见大婶的踪影。
又一周过去了,大婶出现了,我一阵莫名惊喜,但最终还是坐在了吴师这边。擦完鞋,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蹲到大婶旁边选购鞋垫,搭讪中得知,她的孩子病情加重了。
以后的日子,我照例上下班路过,大婶有时出摊,有时不在,这自然影响了她的生意。吴师这边人更多了,甚至排队,她这边多数时间无顾客,不知是嫌她的手艺,还是跟我一样的心理。时间久了,吴师对她的态度好像有所改观,他俩的摊位间距近了些,吴师有时也鼓动顾客到她那边去擦,“她擦得好着呢。”我不知是吴师忙不过来,还是动了恻隐之心。
又过了一年,吴师越发精神,厚厚的头发像他擦的皮鞋一样黑又亮、挺又坚,大婶明显苍老,头上套了纺织帽,脸上捂了蓝口罩。我还是吴师的常客,大婶鞋垫的忠实“粉丝”。时间就这么日复一日地过着,又好一阵没见大婶出摊了,“唉!娃子的病呐,把她整得够呛。”吴师停下正打蜡的手,抬头怔怔地望着我,我蓦然感觉这是一双求救的眼神。
大婶许久没出摊了,擦鞋处只有吴师一人,我坐在对面静静地欣赏他指挥家般的舞动、魔术师似的变幻。“买双鞋垫吧。”我一眼分辨出吴师身旁的包裹和鞋垫都是大婶的。“她儿子住院,急需用钱,我全买过来了,多少钱买的多少钱卖,不赚你钱。”吴师诚恳兜售,我二话没说,全拿了。
吴师每天早出晚归,埋头擦鞋,我依然每天上下班路过,隔三岔五光顾吴师,我已习惯吴师旁边有一个摊位,可大婶很长时间了还没出现。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王健春

喜盈门商场十字路口右拐角,早先只有一个擦鞋的中年男子,敦敦实实,三十来岁,人精干,手麻利,我上下班经过,自然成了常客,每次擦了就走,也没过多交流,擦鞋的都称他“吴师”。
不久,吴师的左侧多了一个擦鞋摊位,是个女的,五十多岁的样子,穿戴还算干净。我每次习惯找吴师,在等待中东张西望,见旁边摊位年轻男子坐在大婶对面,叼着烟,伸出脚,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心里就不舒服。大婶吃力弯腰,好像还用嘴吹,再瞧男子一副悠闲自得、理所当然的享受样子,气更不打一处来,眼睛瞅着,心里骂着,对擦鞋大婶更加怜悯起来,就像自己长辈沦落成给人家擦鞋似的,继而怪怨起大婶及她的家人来,遇到什么大不了的困难,非得出来摆摊擦鞋?干点其他的不行吗?卖菜、做饭、工地小工,都好啊!家里男人呢?再继而为她愤懑、惋惜、鸣不平。
一日,和同事一前一后来擦鞋,我在吴师这儿擦,让他等我擦完,谁知他径直坐到大婶对面,还有说有笑。回去的路上,我责怪他怎么能让大婶擦呢,他一愣?得知我的理由后,笑了。
晚上,躺在床上,转辗回味同事白天说的话,许久,我由困惑转而彻悟:是呀,擦鞋是劳动,有什么不光彩?你让她擦,其实是光顾她生意;你不让她擦,其实是不给她挣钱机会。谁不想挑轻松、干净的活?要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搁着清福在这儿饱经风霜呢?……想着想着,我汗颜了,为自己假善心、真虚伪而惭愧。
以后,到了擦鞋处,心里想着照顾大婶,犹豫片刻后,还是坐在了吴师摊位,我实在拉不下脸让一位大自己十多岁的人为自己擦鞋。日子就这么过着,忽然有一天,擦鞋的又只有吴师一人了。“她,病怏怏,还擦鞋?跟我抢生意?!”吴师边挤油边撇嘴嘟囔,看得出他并不欢迎大婶加入他的行列。一连几天,上下班路过,都不见大婶的踪影。
又一周过去了,大婶出现了,我一阵莫名惊喜,但最终还是坐在了吴师这边。擦完鞋,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蹲到大婶旁边选购鞋垫,搭讪中得知,她的孩子病情加重了。
以后的日子,我照例上下班路过,大婶有时出摊,有时不在,这自然影响了她的生意。吴师这边人更多了,甚至排队,她这边多数时间无顾客,不知是嫌她的手艺,还是跟我一样的心理。时间久了,吴师对她的态度好像有所改观,他俩的摊位间距近了些,吴师有时也鼓动顾客到她那边去擦,“她擦得好着呢。”我不知是吴师忙不过来,还是动了恻隐之心。
又过了一年,吴师越发精神,厚厚的头发像他擦的皮鞋一样黑又亮、挺又坚,大婶明显苍老,头上套了纺织帽,脸上捂了蓝口罩。我还是吴师的常客,大婶鞋垫的忠实“粉丝”。时间就这么日复一日地过着,又好一阵没见大婶出摊了,“唉!娃子的病呐,把她整得够呛。”吴师停下正打蜡的手,抬头怔怔地望着我,我蓦然感觉这是一双求救的眼神。
大婶许久没出摊了,擦鞋处只有吴师一人,我坐在对面静静地欣赏他指挥家般的舞动、魔术师似的变幻。“买双鞋垫吧。”我一眼分辨出吴师身旁的包裹和鞋垫都是大婶的。“她儿子住院,急需用钱,我全买过来了,多少钱买的多少钱卖,不赚你钱。”吴师诚恳兜售,我二话没说,全拿了。
吴师每天早出晚归,埋头擦鞋,我依然每天上下班路过,隔三岔五光顾吴师,我已习惯吴师旁边有一个摊位,可大婶很长时间了还没出现。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