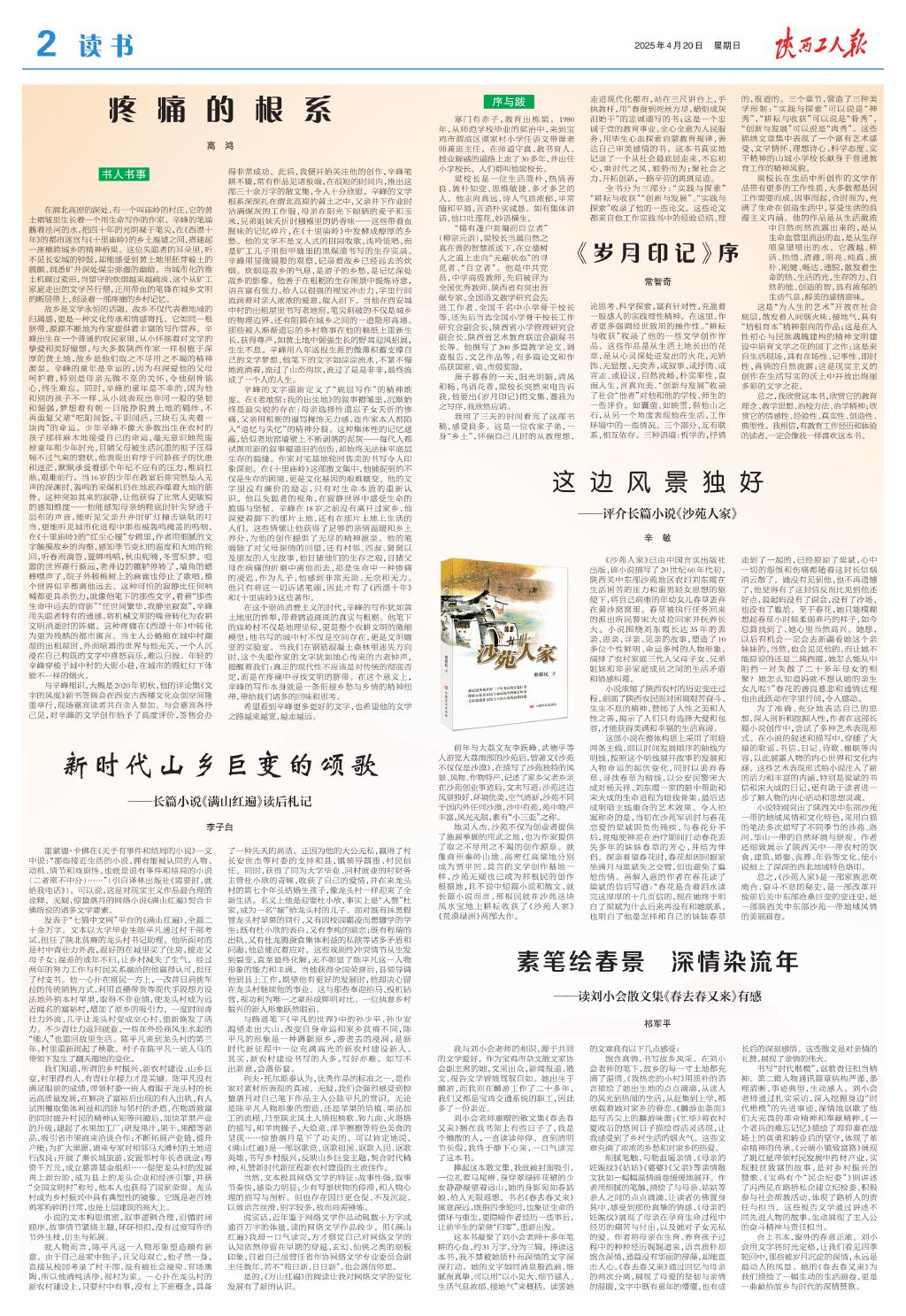疼痛的根系
高鸿
在渭北高原的深处,有一个叫庙岭的村庄,它的黄土褶皱里生长着一个用生命写作的作家。辛峰的笔端蘸着泾河的水,把四十年的光阴凝于笔尖,在《西漂十年》的都市迷宫与《十里庙岭》的乡土废墟之间,搭建起一座横跨城乡的精神桥梁。这位失聪者的耳朵里,听不见长安城的钟鼓,却能感受到黄土地里胚芽破土的震颤,洞悉矿井深处煤尘弥漫的幽暗。当城市化的推土机碾过麦田,当留守的炊烟越来越疏淡,这个从矿工家庭走出的文学苦行僧,正用带血的笔锋在城乡文明的断层带上,刻录着一部疼痛的乡村记忆。
故乡是文学永恒的话题。故乡不仅代表着地域的归属感,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情感寄托。它如同一根脐带,源源不断地为作家提供着丰富的写作营养。辛峰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里,从小怀揣着对文学的挚爱和美好憧憬,与大多数陕西作家一样根植于深厚的黄土地,故乡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辛峰的童年是幸运的,因为有深爱他的父母呵护着,特别是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令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同时,辛峰的童年是不幸的,因为他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从小就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坚韧和倔强,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挣脱黄土地的羁绊,不再重复父辈“吃阳间饭,干阴间活,三块石头夹着一块肉”的命运。少年辛峰不像大多数出生在农村的孩子那样麻木地接受自己的命运,毫无意识地荒废掉童年和少年时光,目睹父母被生活沉重的担子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窘状,他表现出有悖于同龄孩子的忧患和迷茫,默默承受着那个年纪不应有的压力,稚肩扛鼎,艰难前行。当16岁的少年在教室后排突然坠入无声的深渊时,轰鸣的采煤机仍在地底吞噬着大地的筋骨。这种突如其来的寂静,让他获得了比常人更敏锐的感知维度——他能感知母亲纳鞋底时针尖穿透千层布的声音,能听见父亲升井时矿灯撞击铁轨的叮当,更能听见城市化进程中那些被轰鸣掩盖的呜咽。在《十里庙岭》的“红尘心履”专辑里,作者用细腻的文字触摸故乡的沟壑,感知季节变幻的温度和大地的轮回,听春雨滴答,夏蝉鸣唱,秋虫呢喃,冬雪织梦。喧嚣的世界渐行渐远,老井边的辘轳停转了,墙角的蟋蟀噤声了,院子外核桃树上的麻雀也停止了歌唱,整个世界似乎都离他远去。这种可怕的寂静比任何呐喊都更具杀伤力,就像他笔下的那些文字,看着“那些生命中远去的背影”“任世间繁华,我静坐寂寞”,辛峰用失聪者特有的通感,将机械文明的噪音转化为农耕文明消逝时的阵痛。这种疼痛在《西漂十年》中转化为更为残酷的都市寓言。当主人公蜷缩在城中村潮湿的出租屋时,外面喧嚣的世界与他无关,一个人沉浸在自己构筑的文字中喜怒哀乐,难以自拔。年轻的辛峰穿梭于城中村的大街小巷,在城市的霓虹灯下体验不一样的烟火。
与辛峰相识,大概是2020年初秋,他的评论集《文字的风度》新书签售会在西安古西楼文化众创空间隆重举行,现场嘉宾读者共百余人参加。与会嘉宾各抒己见,对辛峰的文学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签售会办得非常成功。此后,我便开始关注他的创作,辛峰笔耕不辍,常有作品见诸报端,在很短的时间内,推出这部三十余万字的散文集,令人十分欣慰。辛峰的文学根系深深扎在渭北高原的黄土之中,父亲井下作业时沾满煤灰的工作服,母亲在阳光下晾晒的麦子和玉米,兄弟姐妹夭折时襁褓里的奶香味——这些带着血腥味的记忆碎片,在《十里庙岭》中发酵成醇厚的乡愁。他的文字不是文人式的田园牧歌,浅吟低唱,而是矿工儿子用指甲缝里的黑煤渣书写的生存实录。辛峰用显微镜般的观察,记录着故乡已经远去的炊烟。炊烟是故乡的气息,是游子的乡愁,是记忆深处故乡的影像。他善于在粗粝的生存图景中提炼诗意,语言富有张力,给人以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字里行间流淌着对亲人浓浓的爱意,催人泪下。当他在西安城中村的出租屋里书写老地窑,笔尖刺破的不仅是城乡的物理边界,还有阻隔在城乡之间的一道隐形高墙。那些被人渐渐遗忘的乡村物事在他的稿纸上重新生长,获得尊严,如黄土地中倔强生长的野蒿迎风招展,生生不息。辛峰用八年送报生涯的微薄积蓄支撑自己的文学梦想,他笔下的文字如淙淙流水,不紧不慢地流淌着,流过了山峦沟坎,流过了是是非非,最终流成了一个人的人生。
辛峰的文字重新定义了“底层写作”的精神维度。在《老地窑:我的出生地》的叙事褶皱里,沉默始终是最尖锐的存在:母亲选择性遗忘子女夭折的惨痛,父亲用粗粝的谩骂掩饰无力感,连作家本人都陷入“追忆与失忆”的精神分裂。这种集体性的记忆遮蔽,恰似老地窑墙壁上不断剥落的泥灰——每代人都试图用新的叙事覆盖旧的创伤,却始终无法抹平底层生存的裂缝。作家对宅基地轮回售卖的书写令人印象深刻。在《十里庙岭》这部散文集中,他捕捉到的不仅是生存的困境,更是文化基因的艰难嬗变。他的文字里没有廉价的励志,只有对生命本质的重新认识。他以失聪者的视角,在寂静世界中感受生命的脆弱与坚韧。辛峰在18岁之前没有离开过家乡,他深爱着脚下的那片土地,还有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这些情愫让他获得了足够的亲情温暖和乡土养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精神源泉。他的笔端除了对父母深情的回望,还有村邻、四叔、舅舅以及朋友的人生故事,他目睹他们的生存之艰,目睹父母在病痛的折磨中离他而去,那是生命中一种惨痛的凌迟,作为儿子,他感到非常无助、无奈和无力。他只有将这一切诉诸笔端,因此才有了《西漂十年》和《十里庙岭》这些著作。
在这个崇尚消费主义的时代,辛峰的写作犹如黄土地里的铧犁,带着锈迹斑斑的真实与粗粝。他笔下的庙岭村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整个农耕文明的微缩模型;他书写的城中村不仅是空间存在,更是文明嬗变的实验室。当我们在钢筋混凝土森林里迷失方向时,这个失聪作家的文字犹如地心传来的古老钟声,提醒着我们:真正的现代性不应该是对传统的彻底否定,而是在疼痛中寻找文明的脐带。在这个意义上,辛峰的写作本身就是一条衔接乡愁与乡情的精神纽带,带给我们诸多的回味和思考。
希望看到辛峰更多更好的文字,也希望他的文学之路越来越宽,越走越远。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高鸿
在渭北高原的深处,有一个叫庙岭的村庄,它的黄土褶皱里生长着一个用生命写作的作家。辛峰的笔端蘸着泾河的水,把四十年的光阴凝于笔尖,在《西漂十年》的都市迷宫与《十里庙岭》的乡土废墟之间,搭建起一座横跨城乡的精神桥梁。这位失聪者的耳朵里,听不见长安城的钟鼓,却能感受到黄土地里胚芽破土的震颤,洞悉矿井深处煤尘弥漫的幽暗。当城市化的推土机碾过麦田,当留守的炊烟越来越疏淡,这个从矿工家庭走出的文学苦行僧,正用带血的笔锋在城乡文明的断层带上,刻录着一部疼痛的乡村记忆。
故乡是文学永恒的话题。故乡不仅代表着地域的归属感,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情感寄托。它如同一根脐带,源源不断地为作家提供着丰富的写作营养。辛峰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里,从小怀揣着对文学的挚爱和美好憧憬,与大多数陕西作家一样根植于深厚的黄土地,故乡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辛峰的童年是幸运的,因为有深爱他的父母呵护着,特别是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令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同时,辛峰的童年是不幸的,因为他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从小就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坚韧和倔强,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挣脱黄土地的羁绊,不再重复父辈“吃阳间饭,干阴间活,三块石头夹着一块肉”的命运。少年辛峰不像大多数出生在农村的孩子那样麻木地接受自己的命运,毫无意识地荒废掉童年和少年时光,目睹父母被生活沉重的担子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窘状,他表现出有悖于同龄孩子的忧患和迷茫,默默承受着那个年纪不应有的压力,稚肩扛鼎,艰难前行。当16岁的少年在教室后排突然坠入无声的深渊时,轰鸣的采煤机仍在地底吞噬着大地的筋骨。这种突如其来的寂静,让他获得了比常人更敏锐的感知维度——他能感知母亲纳鞋底时针尖穿透千层布的声音,能听见父亲升井时矿灯撞击铁轨的叮当,更能听见城市化进程中那些被轰鸣掩盖的呜咽。在《十里庙岭》的“红尘心履”专辑里,作者用细腻的文字触摸故乡的沟壑,感知季节变幻的温度和大地的轮回,听春雨滴答,夏蝉鸣唱,秋虫呢喃,冬雪织梦。喧嚣的世界渐行渐远,老井边的辘轳停转了,墙角的蟋蟀噤声了,院子外核桃树上的麻雀也停止了歌唱,整个世界似乎都离他远去。这种可怕的寂静比任何呐喊都更具杀伤力,就像他笔下的那些文字,看着“那些生命中远去的背影”“任世间繁华,我静坐寂寞”,辛峰用失聪者特有的通感,将机械文明的噪音转化为农耕文明消逝时的阵痛。这种疼痛在《西漂十年》中转化为更为残酷的都市寓言。当主人公蜷缩在城中村潮湿的出租屋时,外面喧嚣的世界与他无关,一个人沉浸在自己构筑的文字中喜怒哀乐,难以自拔。年轻的辛峰穿梭于城中村的大街小巷,在城市的霓虹灯下体验不一样的烟火。
与辛峰相识,大概是2020年初秋,他的评论集《文字的风度》新书签售会在西安古西楼文化众创空间隆重举行,现场嘉宾读者共百余人参加。与会嘉宾各抒己见,对辛峰的文学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签售会办得非常成功。此后,我便开始关注他的创作,辛峰笔耕不辍,常有作品见诸报端,在很短的时间内,推出这部三十余万字的散文集,令人十分欣慰。辛峰的文学根系深深扎在渭北高原的黄土之中,父亲井下作业时沾满煤灰的工作服,母亲在阳光下晾晒的麦子和玉米,兄弟姐妹夭折时襁褓里的奶香味——这些带着血腥味的记忆碎片,在《十里庙岭》中发酵成醇厚的乡愁。他的文字不是文人式的田园牧歌,浅吟低唱,而是矿工儿子用指甲缝里的黑煤渣书写的生存实录。辛峰用显微镜般的观察,记录着故乡已经远去的炊烟。炊烟是故乡的气息,是游子的乡愁,是记忆深处故乡的影像。他善于在粗粝的生存图景中提炼诗意,语言富有张力,给人以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字里行间流淌着对亲人浓浓的爱意,催人泪下。当他在西安城中村的出租屋里书写老地窑,笔尖刺破的不仅是城乡的物理边界,还有阻隔在城乡之间的一道隐形高墙。那些被人渐渐遗忘的乡村物事在他的稿纸上重新生长,获得尊严,如黄土地中倔强生长的野蒿迎风招展,生生不息。辛峰用八年送报生涯的微薄积蓄支撑自己的文学梦想,他笔下的文字如淙淙流水,不紧不慢地流淌着,流过了山峦沟坎,流过了是是非非,最终流成了一个人的人生。
辛峰的文字重新定义了“底层写作”的精神维度。在《老地窑:我的出生地》的叙事褶皱里,沉默始终是最尖锐的存在:母亲选择性遗忘子女夭折的惨痛,父亲用粗粝的谩骂掩饰无力感,连作家本人都陷入“追忆与失忆”的精神分裂。这种集体性的记忆遮蔽,恰似老地窑墙壁上不断剥落的泥灰——每代人都试图用新的叙事覆盖旧的创伤,却始终无法抹平底层生存的裂缝。作家对宅基地轮回售卖的书写令人印象深刻。在《十里庙岭》这部散文集中,他捕捉到的不仅是生存的困境,更是文化基因的艰难嬗变。他的文字里没有廉价的励志,只有对生命本质的重新认识。他以失聪者的视角,在寂静世界中感受生命的脆弱与坚韧。辛峰在18岁之前没有离开过家乡,他深爱着脚下的那片土地,还有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这些情愫让他获得了足够的亲情温暖和乡土养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精神源泉。他的笔端除了对父母深情的回望,还有村邻、四叔、舅舅以及朋友的人生故事,他目睹他们的生存之艰,目睹父母在病痛的折磨中离他而去,那是生命中一种惨痛的凌迟,作为儿子,他感到非常无助、无奈和无力。他只有将这一切诉诸笔端,因此才有了《西漂十年》和《十里庙岭》这些著作。
在这个崇尚消费主义的时代,辛峰的写作犹如黄土地里的铧犁,带着锈迹斑斑的真实与粗粝。他笔下的庙岭村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整个农耕文明的微缩模型;他书写的城中村不仅是空间存在,更是文明嬗变的实验室。当我们在钢筋混凝土森林里迷失方向时,这个失聪作家的文字犹如地心传来的古老钟声,提醒着我们:真正的现代性不应该是对传统的彻底否定,而是在疼痛中寻找文明的脐带。在这个意义上,辛峰的写作本身就是一条衔接乡愁与乡情的精神纽带,带给我们诸多的回味和思考。
希望看到辛峰更多更好的文字,也希望他的文学之路越来越宽,越走越远。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