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线之上的守望
吴双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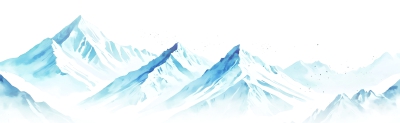
天山腹地:冰与火的青春烙印
独库公路,宛如一条灵动的巨龙,盘桓于天山的雄伟之心,被冠以“中国最美公路”的美誉。如今,它成为了游人的网红打卡胜地。然而,于我而言,这条公路的每一寸曲折,都似一把刻刀,在我的生命里雕琢出永不磨灭的痕迹。
独库公路的第一个关键节点——乔尔玛,隐匿于天山的神秘腹地。在这里,天山公路建设博物馆与乔尔玛烈士陵园静静矗立。它们虽无言,却讲述着这条路背后的尊严与沉重。
时光回溯四十二年,1983年5月,我,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懵懂小伙,以乌鲁木齐军区通信载波员的身份,踏入了乔尔玛机务站这片土地,直至次年3月离去,短短十个月的驻守,却在我的人生长河中铭刻下永恒的印记,每一次回忆,都如同汹涌的浪潮,热泪止不住地奔涌。
乔尔玛的冬天,是严酷的代名词。寒风呼啸,如一把把锋利的刀刃,在裸露的皮肤上肆意切割;积雪深得及膝,每一次巡查线路,都仿若在生死边缘徘徊。生活的底色是单调与匮乏的合奏。餐桌上,萝卜片、白菜片、土豆片这“老三片”,年复一年地唱着“主角”。
闲暇时光何在?看书,是唯一的奢侈享受;锻炼身体,是抵御严寒与无聊的本能之举;守着机器,和年轻的战友们无边无际地“吹牛”,是贫瘠精神世界里微弱却珍贵的火花。然而,与那些在绝壁上开凿天路的工程兵兄弟们相比,我们这些守在机房的通信兵,已算是拥有了莫大的“幸运”。
在乔尔玛度过的十个月,“塌方”“雪崩”“牺牲”……这些沉重的词汇,如同达坂上终年不散的阴霾,一次又一次无情地撞击着我们的心灵。据统计,为了修建独库公路,共有168名战士将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乔尔玛烈士陵园,其中年龄最小的仅有17岁。正是这些默默倒下的年轻生命,用血肉之躯铸就了这条天路,它当之无愧地被誉为“英雄之路”。
乔尔玛:时光的碎片与四季的变奏
乔尔玛的时光,仿若被风撕扯成碎片。在这里,四季的更迭被打破,只有春天与冬天的交替。乔尔玛的天气,就像孩子那捉摸不透的情绪。前一刻还是澄澈的蓝天白云,下一刻便乌云密布,暴雨倾盆,一日之中五六场雨是家常便饭。雨后,最欢愉的莫过于不值班的战友们提着铁桶、端着盆子,兴冲冲地钻进后山去采蘑菇。
营房前横亘着一条沙石路,蜿蜒伸向尼勒克县的方向。路上车影罕至,倒是牛羊悠然自得地踱过,它们的蹄印很快便被风沙轻轻抹去。路的对面,是一片倔强的荆棘林,传说百年间只分枝却不长高,成了野兔们的天然迷宫。穿过荆棘林,喀什河的奔腾声便如潮水般涌进耳畔——河水裹挟着碎冰,汹涌澎湃,唯有冬季,才会迎来片刻的宁静。那时,两岸凝结出琉璃般的冰凌建筑,晶莹剔透,千姿百态,宛如梦幻的水晶宫。河心却倔强地裂开一道缝,恰似大地在冰封之下仍固执地喘息。站在河边眺望远方,天山的雪峰如银剑般直插云霄。越过那些雄伟的雪峰与险峻的冰达坂,便是传说中草浪翻滚的那拉提草原。然而,乔尔玛的官兵们鲜少谈及远方,他们的目光更眷恋于营区外那座喀什河大桥——独库公路的关键咽喉,也是战友们用青春丈量天山的起点。
风雪达坂:孤勇者与意外的馈赠
乔尔玛的严寒与孤寂,却意外地为我这个农家子弟打开了一扇命运之窗。除去值班与查线时间,我把从家乡带来的初高中课本和资料翻得卷了边。一个念头在冻僵的心里顽强燃烧:先把知识夯牢,机会或许会来敲门。
1984年3月初,连队传来消息:总站要举办考军校预备人员培训班,为照顾艰苦边远岗位,决定派遣我和战友汪勇前往乌鲁木齐参加选拔!在乔尔玛的寒夜中,我们常常凑在一起复习、讨论。
从3月6日接到通知,到9日傍晚,鹅毛大雪昼夜不停。考试定在15日!
3月10日拂晓,我和汪勇早早醒来。推开门,心却沉入谷底:天空阴沉,细碎的雪花仍在飘散。“走!拼了!”无需多言,我们异口同声。
我们没有骑马(怕马在深雪中更危险),每人拄一根粗壮的木棍当探路的拐杖,一头扎进了茫茫雪海。一脚下去,积雪瞬间没过小腿。一个多小时后,雪势骤然加大,天地混沌一片,路迹彻底消失。我们只能凭着感觉,用木棍试探着前方的虚实,在白色迷宫中艰难挪动。三个小时过去,体力濒临极限。
终于,我们站在了哈希勒根达坂脚下。为了缓解紧绷的神经,我喘息着对汪勇说:“听说……这附近……有雪莲……”爬行了约三十米,在右后方一个凸起的雪堆上,三朵紫红色的雪莲花,鲜艳得刺眼。
汪勇执意将三朵花都给了我:“你拿着!”后来,这三朵珍贵的雪莲,还真的缓解了母亲多年的老寒腿病痛。
带着雪莲的祝福,我们脚步轻快了些许。不久后,前方风雪中出现了白绿相间的点点——那是筑路部队的帐篷!帐篷里暖意融融,我们休整了近两个小时后,时间已近下午四点,前方还有十四公里,要翻越更险峻的玉希莫勒盖冰达坂。岳副连长坚决不同意我们再徒步冒险,命令一班长骑马护送我们。
于是,三人三骑,朝着那拉提方向继续挺进。大约一小时后,玉希莫勒盖冰达坂那巨大的冰墙横亘在眼前。约两小时后,又一处筑路部队的营地出现在眼前。进去给水壶灌满热水,稍作喘息,再次踏上征途。
一辆草绿色的北京吉普车,正缓缓向我们驶来!那一刻,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冻僵的身体仿佛注入暖流。
晚上八点多,吉普车将我们带到了一个当时还不甚起眼的小村落——后来名扬天下的那拉提。1984年3月10日晚八点左右,我第一次踏足这片尚未被世人熟知的土地。
长明灯:照亮前路的永恒坐标
还是那辆吉普车,将我们安全送达新源县的驻地。短暂休整后,十二日下午,连队的卡车载着我们驶向伊宁市。那也是我第一次领略伊犁河谷的风情。十三日清晨,我和汪勇登上了开往乌鲁木齐的长途班车。当十三日深夜的钟声敲过十二点半,我们终于风尘仆仆地站在了乌鲁木齐的土地上。
后来,我如愿考上了那个宝贵的培训班。三个月的“魔鬼集训”后,我奋力一搏,成功考入了军校,穿上了“四个口袋”的干部服,命运就此改变。
乔尔玛,那个深藏于天山腹地的冰雪驿站,是我人生真正的转折点,是我命运航程扬帆起航的港口。它赋予我的,不仅是军校的通行证,更是钢铁般的意志、对生命的敬畏、对情义的珍视,以及对平凡英雄的无限感念。
四十二年光阴流转,记忆非但未曾褪色,反而在岁月的长河里愈发清晰、滚烫。感谢你,乔尔玛,你是我灵魂深处永恒的坐标。感谢你们,天山深处用生命筑路的战友们,你们铺就的这条“英雄路”,也照亮了我们后来者的征途。感谢汪勇战友,风雪路上生死与共的兄弟!
这段铭刻在天山之巅的经历,是我生命中最厚重的财富。它像那三朵风雪中采撷的雪莲,在记忆的冰峰上,永远绽放着不屈与希望的光芒;它更像乔尔玛烈士陵园里那盏长明灯,在时光的隧道中,恒久地照耀着我余生的每一段路途。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吴双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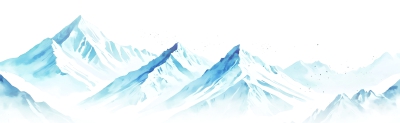
天山腹地:冰与火的青春烙印
独库公路,宛如一条灵动的巨龙,盘桓于天山的雄伟之心,被冠以“中国最美公路”的美誉。如今,它成为了游人的网红打卡胜地。然而,于我而言,这条公路的每一寸曲折,都似一把刻刀,在我的生命里雕琢出永不磨灭的痕迹。
独库公路的第一个关键节点——乔尔玛,隐匿于天山的神秘腹地。在这里,天山公路建设博物馆与乔尔玛烈士陵园静静矗立。它们虽无言,却讲述着这条路背后的尊严与沉重。
时光回溯四十二年,1983年5月,我,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懵懂小伙,以乌鲁木齐军区通信载波员的身份,踏入了乔尔玛机务站这片土地,直至次年3月离去,短短十个月的驻守,却在我的人生长河中铭刻下永恒的印记,每一次回忆,都如同汹涌的浪潮,热泪止不住地奔涌。
乔尔玛的冬天,是严酷的代名词。寒风呼啸,如一把把锋利的刀刃,在裸露的皮肤上肆意切割;积雪深得及膝,每一次巡查线路,都仿若在生死边缘徘徊。生活的底色是单调与匮乏的合奏。餐桌上,萝卜片、白菜片、土豆片这“老三片”,年复一年地唱着“主角”。
闲暇时光何在?看书,是唯一的奢侈享受;锻炼身体,是抵御严寒与无聊的本能之举;守着机器,和年轻的战友们无边无际地“吹牛”,是贫瘠精神世界里微弱却珍贵的火花。然而,与那些在绝壁上开凿天路的工程兵兄弟们相比,我们这些守在机房的通信兵,已算是拥有了莫大的“幸运”。
在乔尔玛度过的十个月,“塌方”“雪崩”“牺牲”……这些沉重的词汇,如同达坂上终年不散的阴霾,一次又一次无情地撞击着我们的心灵。据统计,为了修建独库公路,共有168名战士将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乔尔玛烈士陵园,其中年龄最小的仅有17岁。正是这些默默倒下的年轻生命,用血肉之躯铸就了这条天路,它当之无愧地被誉为“英雄之路”。
乔尔玛:时光的碎片与四季的变奏
乔尔玛的时光,仿若被风撕扯成碎片。在这里,四季的更迭被打破,只有春天与冬天的交替。乔尔玛的天气,就像孩子那捉摸不透的情绪。前一刻还是澄澈的蓝天白云,下一刻便乌云密布,暴雨倾盆,一日之中五六场雨是家常便饭。雨后,最欢愉的莫过于不值班的战友们提着铁桶、端着盆子,兴冲冲地钻进后山去采蘑菇。
营房前横亘着一条沙石路,蜿蜒伸向尼勒克县的方向。路上车影罕至,倒是牛羊悠然自得地踱过,它们的蹄印很快便被风沙轻轻抹去。路的对面,是一片倔强的荆棘林,传说百年间只分枝却不长高,成了野兔们的天然迷宫。穿过荆棘林,喀什河的奔腾声便如潮水般涌进耳畔——河水裹挟着碎冰,汹涌澎湃,唯有冬季,才会迎来片刻的宁静。那时,两岸凝结出琉璃般的冰凌建筑,晶莹剔透,千姿百态,宛如梦幻的水晶宫。河心却倔强地裂开一道缝,恰似大地在冰封之下仍固执地喘息。站在河边眺望远方,天山的雪峰如银剑般直插云霄。越过那些雄伟的雪峰与险峻的冰达坂,便是传说中草浪翻滚的那拉提草原。然而,乔尔玛的官兵们鲜少谈及远方,他们的目光更眷恋于营区外那座喀什河大桥——独库公路的关键咽喉,也是战友们用青春丈量天山的起点。
风雪达坂:孤勇者与意外的馈赠
乔尔玛的严寒与孤寂,却意外地为我这个农家子弟打开了一扇命运之窗。除去值班与查线时间,我把从家乡带来的初高中课本和资料翻得卷了边。一个念头在冻僵的心里顽强燃烧:先把知识夯牢,机会或许会来敲门。
1984年3月初,连队传来消息:总站要举办考军校预备人员培训班,为照顾艰苦边远岗位,决定派遣我和战友汪勇前往乌鲁木齐参加选拔!在乔尔玛的寒夜中,我们常常凑在一起复习、讨论。
从3月6日接到通知,到9日傍晚,鹅毛大雪昼夜不停。考试定在15日!
3月10日拂晓,我和汪勇早早醒来。推开门,心却沉入谷底:天空阴沉,细碎的雪花仍在飘散。“走!拼了!”无需多言,我们异口同声。
我们没有骑马(怕马在深雪中更危险),每人拄一根粗壮的木棍当探路的拐杖,一头扎进了茫茫雪海。一脚下去,积雪瞬间没过小腿。一个多小时后,雪势骤然加大,天地混沌一片,路迹彻底消失。我们只能凭着感觉,用木棍试探着前方的虚实,在白色迷宫中艰难挪动。三个小时过去,体力濒临极限。
终于,我们站在了哈希勒根达坂脚下。为了缓解紧绷的神经,我喘息着对汪勇说:“听说……这附近……有雪莲……”爬行了约三十米,在右后方一个凸起的雪堆上,三朵紫红色的雪莲花,鲜艳得刺眼。
汪勇执意将三朵花都给了我:“你拿着!”后来,这三朵珍贵的雪莲,还真的缓解了母亲多年的老寒腿病痛。
带着雪莲的祝福,我们脚步轻快了些许。不久后,前方风雪中出现了白绿相间的点点——那是筑路部队的帐篷!帐篷里暖意融融,我们休整了近两个小时后,时间已近下午四点,前方还有十四公里,要翻越更险峻的玉希莫勒盖冰达坂。岳副连长坚决不同意我们再徒步冒险,命令一班长骑马护送我们。
于是,三人三骑,朝着那拉提方向继续挺进。大约一小时后,玉希莫勒盖冰达坂那巨大的冰墙横亘在眼前。约两小时后,又一处筑路部队的营地出现在眼前。进去给水壶灌满热水,稍作喘息,再次踏上征途。
一辆草绿色的北京吉普车,正缓缓向我们驶来!那一刻,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冻僵的身体仿佛注入暖流。
晚上八点多,吉普车将我们带到了一个当时还不甚起眼的小村落——后来名扬天下的那拉提。1984年3月10日晚八点左右,我第一次踏足这片尚未被世人熟知的土地。
长明灯:照亮前路的永恒坐标
还是那辆吉普车,将我们安全送达新源县的驻地。短暂休整后,十二日下午,连队的卡车载着我们驶向伊宁市。那也是我第一次领略伊犁河谷的风情。十三日清晨,我和汪勇登上了开往乌鲁木齐的长途班车。当十三日深夜的钟声敲过十二点半,我们终于风尘仆仆地站在了乌鲁木齐的土地上。
后来,我如愿考上了那个宝贵的培训班。三个月的“魔鬼集训”后,我奋力一搏,成功考入了军校,穿上了“四个口袋”的干部服,命运就此改变。
乔尔玛,那个深藏于天山腹地的冰雪驿站,是我人生真正的转折点,是我命运航程扬帆起航的港口。它赋予我的,不仅是军校的通行证,更是钢铁般的意志、对生命的敬畏、对情义的珍视,以及对平凡英雄的无限感念。
四十二年光阴流转,记忆非但未曾褪色,反而在岁月的长河里愈发清晰、滚烫。感谢你,乔尔玛,你是我灵魂深处永恒的坐标。感谢你们,天山深处用生命筑路的战友们,你们铺就的这条“英雄路”,也照亮了我们后来者的征途。感谢汪勇战友,风雪路上生死与共的兄弟!
这段铭刻在天山之巅的经历,是我生命中最厚重的财富。它像那三朵风雪中采撷的雪莲,在记忆的冰峰上,永远绽放着不屈与希望的光芒;它更像乔尔玛烈士陵园里那盏长明灯,在时光的隧道中,恒久地照耀着我余生的每一段路途。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