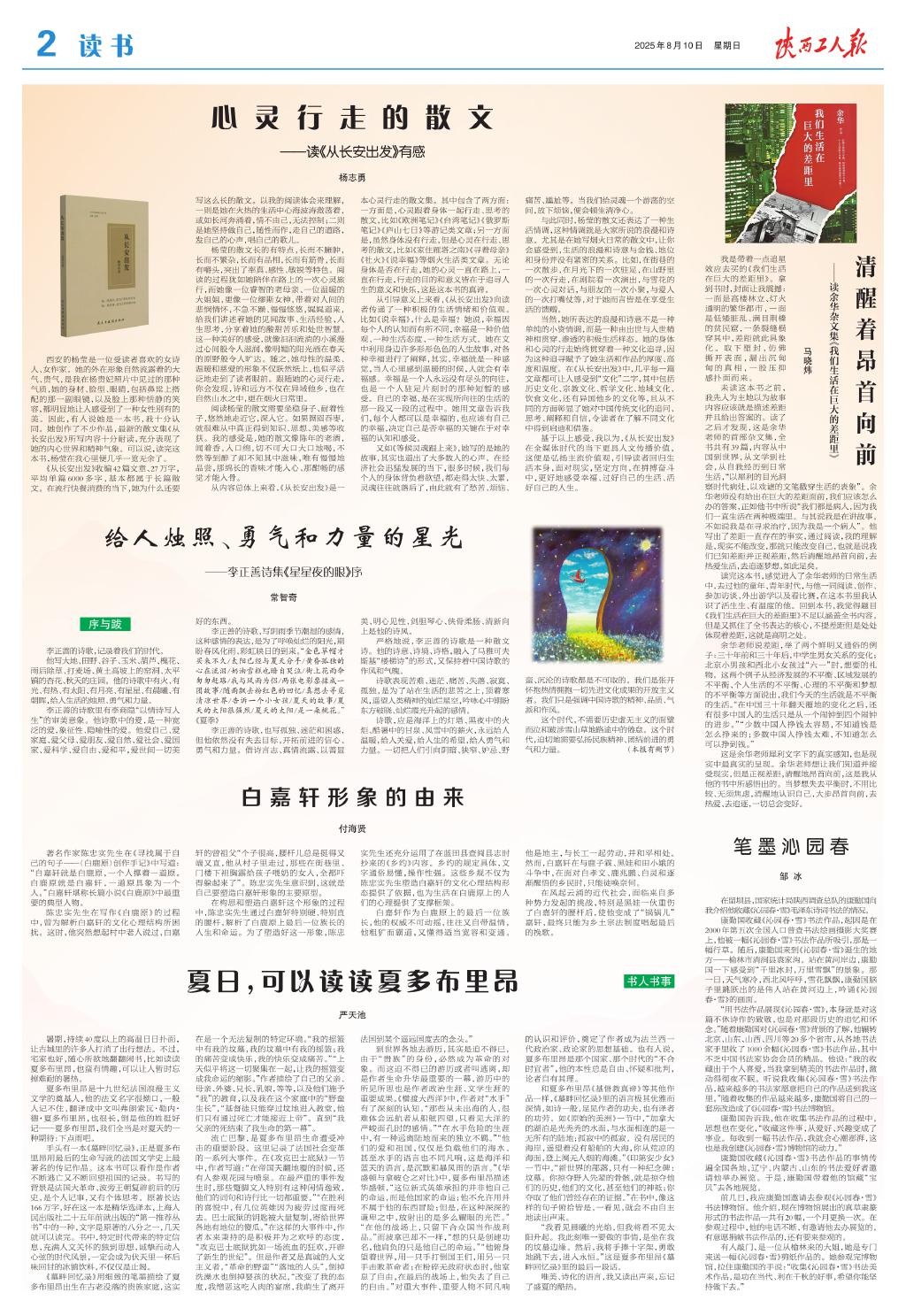夏日,可以读读夏多布里昂
严天池
暑期,持续40度以上的高温日日扑面,让古城里的许多人打消了出行想法。不过,宅家也好,随心所欲地翻翻闲书,比如读读夏多布里昂,也蛮有情趣,可以让人暂时忘掉难耐的暑热。
夏多布里昂是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法文名字很拗口,一般人记不住,翻译成中文叫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也很长,倒是他的姓挺好记——夏多布里昂,我们全当是对夏天的一种期待:下点雨吧。
手头有一本《墓畔回忆录》,正是夏多布里昂用最后的生命写就的法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传记作品。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作者不断逃亡又不断回望祖国的记录。书写的背景是法国大革命、波旁王朝复辟前后的历史,是个人记事,又有个体思考。原著长达166万字,好在这一本是精华选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十五年前就出版的“第一推荐丛书”中的一种,文字是原著的八分之一,几天就可以读完。书中,特定时代带来的特定信息,充满人文关怀的独到思想,诚挚而动人心弦的时代风景,一定会成为伏天里一杯后味回甘的冰镇饮料,不仅仅是止渴。
《墓畔回忆录》用细致的笔墨描绘了夏多布里昂出生在古老没落的贵族家庭,这实在是一个无法复制的特定环境。“我的摇篮中有我的坟墓,我的坟墓中有我的摇篮;我的痛苦变成快乐,我的快乐变成痛苦。”“上天似乎将这一切聚集在一起,让我的摇篮变成我命运的缩影。”作者描绘了自己的父亲、母亲、外婆、兄长、乳娘,等等,以及他们施予“我”的教育,以及我在这个家庭中的“野蛮生长”,“基督徒只能穿过坟地进入教堂,他们只有通过死亡才能接近上帝”。直到“我父亲的死结束了我生命的第一幕”。
流亡巴黎,是夏多布里昂生命遭受冲击的重要阶段。这里记录了法国社会变革的一系列大事件。在《攻克巴士底狱》一节中,作者写道:“在帝国天翻地覆的时候,还有人参观花园与喷泉。在最严重的事件发生时,那些蹩脚文人特别有这种闲情逸致,他们的词句和诗行比一切都重要。”“在胜利的喜悦中,有几位英雄因为疲劳过度而死去。巴士底狱的钥匙被大量复制,寄给世界各地有地位的傻瓜。”在这样的大事件中,作者本来秉持的是积极并为之欢呼的态度,“攻克巴士底狱犹如一场流血的狂欢,开辟了新生的世纪”。但是作者又是真诚的人文主义者,“革命的野蛮”“落地的人头”,倒掉洗澡水也倒掉婴孩的状况,“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憎恶这吃人肉的宴席,我萌生了离开法国到某个遥远国度去的念头。”
到世界各地去游历,其实是迫不得已,由于“贵族”的身份,必然成为革命的对象。而这迫不得已的游历或者叫逃离,却是作者生命升华最重要的一幕,游历中的所见所思也是作者政治生涯、文学生涯的重要成果。《横渡大西洋》中,作者对“水手”有了深刻的认知。“那些从未出海的人,很难体会远航者从船舷四望,只看见大洋的严峻面孔时的感情。”“在水手危险的生涯中,有一种远离陆地而来的独立不羁。”“他们的爱和祖国,仅仅是负载他们的海水。甚至水手的语言也不同凡响,这是海洋和蓝天的语言,是沉默和暴风雨的语言。”《华盛顿与拿破仑之对比》中,夏多布里昂描述华盛顿,“这位新式英雄承担的并非他自己的命运,而是他国家的命运;他不允许用并不属于他的东西冒险;但是,在这种深深的谦卑之中,放射出的是多么耀眼的光芒。”“在他的战场上,只留下合众国当作战利品。”而波拿巴却不一样,“想的只是创建功名,他肩负的只是他自己的命运。”“他俯身望着世界,用一只手打倒国王们,用另一只手击败革命者;在粉碎无政府状态时,他窒息了自由,在最后的战场上,他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对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不同凡响的认识和评价,奠定了作者成为法兰西一代政治家、政论家的思想基础。也有人说,夏多布里昂是那个国家、那个时代的“不合时宜者”,他的本性总是自由、怀疑和批判,论者自有其理。
和夏多布里昂《基督教真谛》等其他作品一样,《墓畔回忆录》里的语言极其优雅而深情,如诗一般,足见作者的功夫,也有译者的功劳。如《原始的美洲》一节中,“加拿大的湖泊是光秃秃的水面,与水面相连的是一无所有的陆地;孤寂中的孤寂。没有居民的海岸,遥望着没有船舶的大海,你从荒凉的海面,登上阒无人烟的海滩。”《印第安少女》一节中,“新世界的部落,只有一种纪念碑:坟墓。你掠夺野人先辈的骨骸,就是掠夺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文化,甚至他们的神祗;你夺取了他们曾经存在的证据。”在书中,像这样的句子俯拾皆是,一看见,就会不由自主地读出声来。
“我看见晨曦的光焰,但我将看不见太阳升起。我此刻唯一要做的事情,是坐在我的坟墓边缘。然后,我将手捧十字架,勇敢地跳下去,进入永恒。”这是夏多布里昂《墓畔回忆录》里的最后一段话。
唯美、诗化的语言,我又读出声来,忘记了盛夏的酷热。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严天池
暑期,持续40度以上的高温日日扑面,让古城里的许多人打消了出行想法。不过,宅家也好,随心所欲地翻翻闲书,比如读读夏多布里昂,也蛮有情趣,可以让人暂时忘掉难耐的暑热。
夏多布里昂是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法文名字很拗口,一般人记不住,翻译成中文叫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也很长,倒是他的姓挺好记——夏多布里昂,我们全当是对夏天的一种期待:下点雨吧。
手头有一本《墓畔回忆录》,正是夏多布里昂用最后的生命写就的法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传记作品。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作者不断逃亡又不断回望祖国的记录。书写的背景是法国大革命、波旁王朝复辟前后的历史,是个人记事,又有个体思考。原著长达166万字,好在这一本是精华选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十五年前就出版的“第一推荐丛书”中的一种,文字是原著的八分之一,几天就可以读完。书中,特定时代带来的特定信息,充满人文关怀的独到思想,诚挚而动人心弦的时代风景,一定会成为伏天里一杯后味回甘的冰镇饮料,不仅仅是止渴。
《墓畔回忆录》用细致的笔墨描绘了夏多布里昂出生在古老没落的贵族家庭,这实在是一个无法复制的特定环境。“我的摇篮中有我的坟墓,我的坟墓中有我的摇篮;我的痛苦变成快乐,我的快乐变成痛苦。”“上天似乎将这一切聚集在一起,让我的摇篮变成我命运的缩影。”作者描绘了自己的父亲、母亲、外婆、兄长、乳娘,等等,以及他们施予“我”的教育,以及我在这个家庭中的“野蛮生长”,“基督徒只能穿过坟地进入教堂,他们只有通过死亡才能接近上帝”。直到“我父亲的死结束了我生命的第一幕”。
流亡巴黎,是夏多布里昂生命遭受冲击的重要阶段。这里记录了法国社会变革的一系列大事件。在《攻克巴士底狱》一节中,作者写道:“在帝国天翻地覆的时候,还有人参观花园与喷泉。在最严重的事件发生时,那些蹩脚文人特别有这种闲情逸致,他们的词句和诗行比一切都重要。”“在胜利的喜悦中,有几位英雄因为疲劳过度而死去。巴士底狱的钥匙被大量复制,寄给世界各地有地位的傻瓜。”在这样的大事件中,作者本来秉持的是积极并为之欢呼的态度,“攻克巴士底狱犹如一场流血的狂欢,开辟了新生的世纪”。但是作者又是真诚的人文主义者,“革命的野蛮”“落地的人头”,倒掉洗澡水也倒掉婴孩的状况,“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憎恶这吃人肉的宴席,我萌生了离开法国到某个遥远国度去的念头。”
到世界各地去游历,其实是迫不得已,由于“贵族”的身份,必然成为革命的对象。而这迫不得已的游历或者叫逃离,却是作者生命升华最重要的一幕,游历中的所见所思也是作者政治生涯、文学生涯的重要成果。《横渡大西洋》中,作者对“水手”有了深刻的认知。“那些从未出海的人,很难体会远航者从船舷四望,只看见大洋的严峻面孔时的感情。”“在水手危险的生涯中,有一种远离陆地而来的独立不羁。”“他们的爱和祖国,仅仅是负载他们的海水。甚至水手的语言也不同凡响,这是海洋和蓝天的语言,是沉默和暴风雨的语言。”《华盛顿与拿破仑之对比》中,夏多布里昂描述华盛顿,“这位新式英雄承担的并非他自己的命运,而是他国家的命运;他不允许用并不属于他的东西冒险;但是,在这种深深的谦卑之中,放射出的是多么耀眼的光芒。”“在他的战场上,只留下合众国当作战利品。”而波拿巴却不一样,“想的只是创建功名,他肩负的只是他自己的命运。”“他俯身望着世界,用一只手打倒国王们,用另一只手击败革命者;在粉碎无政府状态时,他窒息了自由,在最后的战场上,他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对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不同凡响的认识和评价,奠定了作者成为法兰西一代政治家、政论家的思想基础。也有人说,夏多布里昂是那个国家、那个时代的“不合时宜者”,他的本性总是自由、怀疑和批判,论者自有其理。
和夏多布里昂《基督教真谛》等其他作品一样,《墓畔回忆录》里的语言极其优雅而深情,如诗一般,足见作者的功夫,也有译者的功劳。如《原始的美洲》一节中,“加拿大的湖泊是光秃秃的水面,与水面相连的是一无所有的陆地;孤寂中的孤寂。没有居民的海岸,遥望着没有船舶的大海,你从荒凉的海面,登上阒无人烟的海滩。”《印第安少女》一节中,“新世界的部落,只有一种纪念碑:坟墓。你掠夺野人先辈的骨骸,就是掠夺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文化,甚至他们的神祗;你夺取了他们曾经存在的证据。”在书中,像这样的句子俯拾皆是,一看见,就会不由自主地读出声来。
“我看见晨曦的光焰,但我将看不见太阳升起。我此刻唯一要做的事情,是坐在我的坟墓边缘。然后,我将手捧十字架,勇敢地跳下去,进入永恒。”这是夏多布里昂《墓畔回忆录》里的最后一段话。
唯美、诗化的语言,我又读出声来,忘记了盛夏的酷热。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