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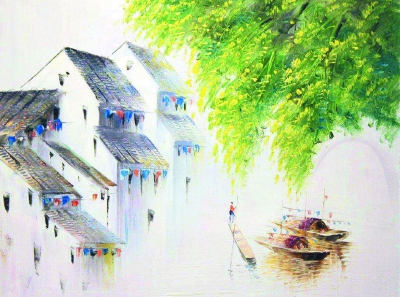
我偶或回乡,遇到的大多都是陌生的面孔。记忆中一棒槌高的孩子,而今已是满脸沧桑、褶皱横竖的爷爷了。很多人需要询问,才能得知他是谁;也有不少人即使询问过,得到了答案,尽管点头允诺着,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但其实还是未搞明白他是谁。
搞不懂谁是谁,对我而言,也许只是小事一桩;但对于村民而言,却是涉及尊严的大事。
年少时,不止一次,我亲耳聆听到村民们聚在一起,对那些离开本村手端公家饭碗的人,挨个予以点评,并对他们进行道德的评判。或曰:某某某很不错,没忘本;或曰:某某某就是个白眼狼,忘本了。
紧随肯定或否定语调的,是众声的附和,其中有赞赏、有叹惋、有唾骂,甚至于不乏诅咒。
何为“忘本”,又何为“没忘本”?究其依据,不过是某次路遇,前者热情地向他打了招呼;而后者,却对他眼睁睁地无视,未予搭理。
以打不打招呼为论据,从而得出是“忘本”还是“未忘本”的结论,未免过于草率和牵强。但我自那时起,就将这些议论视作长鸣的警钟,并时刻忠告自己:无论自己内心是愉悦,还是郁闷,见了村民都要热情似火。然而,百密难免一疏,一个人即使再全神贯注,也会有神思恍惚的时候。也许,就在觉得对面走过来的人有点儿面熟,犹疑是否就是村里的某某某时,问候的良机已经错失。在不断地错失中,我不能排除自己已沦为遭人唾弃可耻的“忘本”者。
人一阔,脸就变,既是做人之忌讳,也是公众之嫉恨。我未阔绰,更未腾达,但在很多土中刨食的村民看来,凡怀揣一个城市户口本的人,无不嘴角斜抽,眼角飞翘,呈现着高高在上的傲慢姿态。
于是甜言蜜语极易换来村民的高调赞颂;热热乎乎很容易转化为“不忘本”的证据。
这种简单化的认知,忽视了人与人之间个性的差异,更是等级社会衍生出的生命之悲和精神之哀。
事实上,在世俗化的世界里,趋炎附势、媚红蔑黑,并非什么新闻,而是生活的常情常态。强者只在乎更强者对自己的态度,却对弱势者的热颜与冷脸往往并不在意。但弱者则大为不同,他们中的很多人,皆拥有一颗玻璃般易碎的心,对强者对自己的表情,显得格外敏感。一个不经意的眼神,一句有口无心的话语,都能化为锋利的箭矢,射中他们的心口。
“忘本”与“不忘本”之论,正是在这样的现实鸡窝里孵化出来的鸡蛋。
不能责怪村民,居于社会末端的他们,实在是被忽略得太久太严重了,他们渴望被尊重、被看得起,并非非分之妄念,而是作为人最低限度的期盼。当然,也不能过度责备那些没有向村民嘘寒问暖的在外务工者,也许他们真的没有留意到迎面走过来的那个人,就是自己往昔的近邻。
阻隔产生陌生,错位产生误解。要让鹰理解兔子为何不飞翔,或让兔子理解鹰为何不在地上跑,既白费力气,又纯属多余。
当我有时候向旁人询问刚和我打招呼的人是谁时,我能感觉出他的惊骇:就是那个谁谁谁呀?你咋搞的,竟连他都忘了?你不会是装的吧?
在记忆深处反复搜索并打捞,的确能捕捉到一些有关谁谁谁的模糊残片。把一个一个的残片拼接起来,才能勾画出谁谁谁那副已经斑驳得犹如古壁画的大致轮廓。
这等窘境,和“装”与“不装”无关,只涉及于记性的牢固与否。
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人和人之间,亲密无间,不亲密亦无间。别家的一切,事无巨细,皆能看在眼里、挂在嘴边,成为东家长西家短的热烈谈资,并迅速被全村所有吸尘器一般的耳朵悉数接收。然而,我却持久地浸泡于与村庄迥然有别的观念池塘之中,这里是人的汪洋,也是信息的大海。在一个与村庄毫无瓜葛的社交体系里,人们不关心你的过去,只在意你的现在;不关心蔬菜的长势,只在意蔬菜的价格;不关心麦子是怎么碾打,只在意面粉里有无添加剂;不关心墙根地畔引发的纠纷,却对官场的勾心斗角和国国之间的冲突津津乐道……如此这般,自然也就没有人在与我的交流中,涉及村庄的家长里短。数十年里,从未有人向我提及过谁谁谁,我又如何能做到让他恒久地盘踞于心?尽管我也在尽力地抗拒着遗忘,但记忆却越来越依稀,越来越渺茫,终究会被时光飘落的积尘彻底覆盖。
小时候背诵过的诗篇,如果不温习、不复诵,注定就会遭到新物事的挤兑和驱逐。人也是一样,如果彼此间久久地不来不往,曾经无比熟悉的人,也会渐渐地沦为记忆深处一缕飘忽的炊烟,消失于无形。□安黎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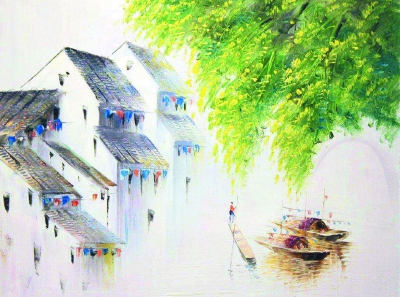
我偶或回乡,遇到的大多都是陌生的面孔。记忆中一棒槌高的孩子,而今已是满脸沧桑、褶皱横竖的爷爷了。很多人需要询问,才能得知他是谁;也有不少人即使询问过,得到了答案,尽管点头允诺着,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但其实还是未搞明白他是谁。
搞不懂谁是谁,对我而言,也许只是小事一桩;但对于村民而言,却是涉及尊严的大事。
年少时,不止一次,我亲耳聆听到村民们聚在一起,对那些离开本村手端公家饭碗的人,挨个予以点评,并对他们进行道德的评判。或曰:某某某很不错,没忘本;或曰:某某某就是个白眼狼,忘本了。
紧随肯定或否定语调的,是众声的附和,其中有赞赏、有叹惋、有唾骂,甚至于不乏诅咒。
何为“忘本”,又何为“没忘本”?究其依据,不过是某次路遇,前者热情地向他打了招呼;而后者,却对他眼睁睁地无视,未予搭理。
以打不打招呼为论据,从而得出是“忘本”还是“未忘本”的结论,未免过于草率和牵强。但我自那时起,就将这些议论视作长鸣的警钟,并时刻忠告自己:无论自己内心是愉悦,还是郁闷,见了村民都要热情似火。然而,百密难免一疏,一个人即使再全神贯注,也会有神思恍惚的时候。也许,就在觉得对面走过来的人有点儿面熟,犹疑是否就是村里的某某某时,问候的良机已经错失。在不断地错失中,我不能排除自己已沦为遭人唾弃可耻的“忘本”者。
人一阔,脸就变,既是做人之忌讳,也是公众之嫉恨。我未阔绰,更未腾达,但在很多土中刨食的村民看来,凡怀揣一个城市户口本的人,无不嘴角斜抽,眼角飞翘,呈现着高高在上的傲慢姿态。
于是甜言蜜语极易换来村民的高调赞颂;热热乎乎很容易转化为“不忘本”的证据。
这种简单化的认知,忽视了人与人之间个性的差异,更是等级社会衍生出的生命之悲和精神之哀。
事实上,在世俗化的世界里,趋炎附势、媚红蔑黑,并非什么新闻,而是生活的常情常态。强者只在乎更强者对自己的态度,却对弱势者的热颜与冷脸往往并不在意。但弱者则大为不同,他们中的很多人,皆拥有一颗玻璃般易碎的心,对强者对自己的表情,显得格外敏感。一个不经意的眼神,一句有口无心的话语,都能化为锋利的箭矢,射中他们的心口。
“忘本”与“不忘本”之论,正是在这样的现实鸡窝里孵化出来的鸡蛋。
不能责怪村民,居于社会末端的他们,实在是被忽略得太久太严重了,他们渴望被尊重、被看得起,并非非分之妄念,而是作为人最低限度的期盼。当然,也不能过度责备那些没有向村民嘘寒问暖的在外务工者,也许他们真的没有留意到迎面走过来的那个人,就是自己往昔的近邻。
阻隔产生陌生,错位产生误解。要让鹰理解兔子为何不飞翔,或让兔子理解鹰为何不在地上跑,既白费力气,又纯属多余。
当我有时候向旁人询问刚和我打招呼的人是谁时,我能感觉出他的惊骇:就是那个谁谁谁呀?你咋搞的,竟连他都忘了?你不会是装的吧?
在记忆深处反复搜索并打捞,的确能捕捉到一些有关谁谁谁的模糊残片。把一个一个的残片拼接起来,才能勾画出谁谁谁那副已经斑驳得犹如古壁画的大致轮廓。
这等窘境,和“装”与“不装”无关,只涉及于记性的牢固与否。
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人和人之间,亲密无间,不亲密亦无间。别家的一切,事无巨细,皆能看在眼里、挂在嘴边,成为东家长西家短的热烈谈资,并迅速被全村所有吸尘器一般的耳朵悉数接收。然而,我却持久地浸泡于与村庄迥然有别的观念池塘之中,这里是人的汪洋,也是信息的大海。在一个与村庄毫无瓜葛的社交体系里,人们不关心你的过去,只在意你的现在;不关心蔬菜的长势,只在意蔬菜的价格;不关心麦子是怎么碾打,只在意面粉里有无添加剂;不关心墙根地畔引发的纠纷,却对官场的勾心斗角和国国之间的冲突津津乐道……如此这般,自然也就没有人在与我的交流中,涉及村庄的家长里短。数十年里,从未有人向我提及过谁谁谁,我又如何能做到让他恒久地盘踞于心?尽管我也在尽力地抗拒着遗忘,但记忆却越来越依稀,越来越渺茫,终究会被时光飘落的积尘彻底覆盖。
小时候背诵过的诗篇,如果不温习、不复诵,注定就会遭到新物事的挤兑和驱逐。人也是一样,如果彼此间久久地不来不往,曾经无比熟悉的人,也会渐渐地沦为记忆深处一缕飘忽的炊烟,消失于无形。□安黎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