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谷听足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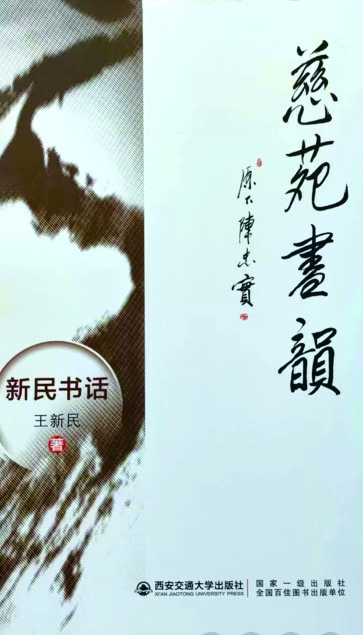
王新民长期在出版界工作,整天与书打交道,写书话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再说他也热衷于写点书话。前不久,又为读者奉献出这部分为“慈苑书韵”“说平论凹”“书评书话”“书友情深”“书生自道”和“书市见闻”等六辑的著作《新民书话》。
书话,是既古老又年轻的文体。说古老,是指书话在历史上早就存在,著名的有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还有清代王士禛的《带经堂诗话》,袁枚的《随园诗话》等,这些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话,却是我国书话文体的开端。到了近代,影响比较大的有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和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书话逐渐规范起来;说年轻,书话到了现当代才独立成为一种文体,名著有周作人的《知堂书话》,叶灵凤的《读书随笔》《北窗读书录》,还有唐弢的《晦庵书话》等,而黄裳、姜德明等则是当代书话的大家,孙犁先生的《书衣文录》把书话写作再次推向新的阶段。
书话的写作,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作者要具有相当深厚的人文素养;二是要懂得关于书的知识;三是熟悉和了解书的作者及创作情况——新民具备了这三个条件,而且还有一个“出版人”的身份,这对他写作书话是非常有利的。所以,写出了这部厚重且文笔轻灵的书话作品。
新民爱书,喜欢读书,他在《购书》里说:“我从小爱书,自家的书不足便借之,借之不足则购之。”这句话看起来平淡,其实却是读书人大都经历过的三个阶段。尤其是在西部边远的乡村,一般来说,家里都存有几本书,然而,这远远不能够满足处在如饥似渴阅读阶段的少年的求知欲,只能借书和买书。我也有过新民这样的经历,知道这句话中蕴含着太多太多为了寻找书的人生故事。爱书,是读书人的天性,若没有这样的天性,则始终与书无缘,即是有缘也很快消失。他说,上街往往是“望商店而却步,见书店而趋步”,可见,新民与书的缘分确实不浅。
读书,犹如登塔,登得一层,眼界就宽了一层,一层一层地登,眼界就一层一层地宽,眼界宽了,想要知道的事就多了,而要知悉这些事,就得不断地读书,而“更上一层楼”的兴趣便越来越大,书也便越读越多,这是读书人永远不能逃脱的“宿命”。读了这么多书,也许有用,也许没有用,不过可以肯定地说,读书人的文化素养便日益提高,这是确凿无疑的。有了较高的文化素养,无他,至少为写书话奠定了基础,不是吗?你看新民,没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能写出这样漂亮的书话?
新民有幸,大学毕业至今一直在出版界,这对一个爱书和喜欢读书的人来说,绝对是个好去处。出版社是“生产”书的地方,新民由此而掌握了关于书的系统而规范的知识,别的不说,至少能鉴别来书好坏,这个好坏,当然是指书的内容。日常生活在书的世界里,好的书也就是内容上乘的书,先睹为快,日子久了,侵染得心灵更美了,因而,读新民的书话,总觉他涉及的人和书,都是天底下的值得“话”的人和书。他笔下的人物,有不少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都曾经叱咤风云,就是没有叱咤过风云,也能留下令人瞩目的成绩。书是人写的。新民由此认识了不少作家或者写书的朋友,知道了不少这些作家和朋友书后的故事或者掌故,这对他写书话,增添了许多有趣的题材,比如,他的《陈彦的创作经验》《怀念京夫》《乡村的吟唱者-和谷印象记》等篇什,就写得引人入胜。
写书话,要有明确的价值观和艺术观,也就是上边所说的能鉴别来书的好坏,书话家要敢于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新民的书话,其中有不少篇章是评论文章,例如《怀念海燕老师——读<青春的备忘>有忆》《行看流水坐看云——<李浩作品系列>读后感》《大美秦岭民族魂——<云横秦岭>阅后记》等,都能抓住书的核心,进行研究和探讨。他评价著名散文家孔明先生的《书中最相思》连及作者,情不自禁地说:“孔明‘他就是一个书生,一个饱读诗书的书生,一个有情有爱的可爱的书生’”——这话说得真确,孔明也是我敬重的朋友,多年交往,印证了新民所言不虚。
收到新民快递来的这部书,在微信上我发给他这样一句话“你复活了陕西的书话文体”——这句话不是随便一说,而是经过认真思考的。现在,专门从事书话写作的作家不多,新民这部著作可称之为“空谷足音”,自然有其价值和意义。
再说点题外话,我国文学史上,有专门的小说史、散文史、诗歌史和戏剧史,而没有专门的书话史。这是因为书话的总量没有其他文体大和多,要写书话史材料不足。但是书话并非没有专门写史的价值。从古到今,书话虽然不属于主流文学,却是独有其思想和艺术价值的文体,除过专门的书话作家的著作而外,几乎所有作家都参与了这个文体的写作,留下了大量值得甄别和整理的文本,如果能做这样的工作,我想,就书话写一部专门史,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好的文学研究的“补缺”工作。之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希望有人能下苦功夫,来做这样的事情。□柏峰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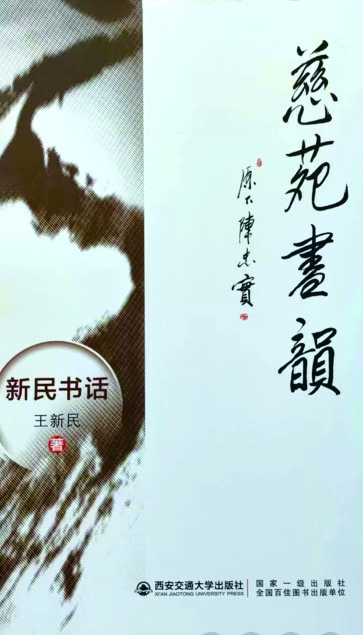
王新民长期在出版界工作,整天与书打交道,写书话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再说他也热衷于写点书话。前不久,又为读者奉献出这部分为“慈苑书韵”“说平论凹”“书评书话”“书友情深”“书生自道”和“书市见闻”等六辑的著作《新民书话》。
书话,是既古老又年轻的文体。说古老,是指书话在历史上早就存在,著名的有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还有清代王士禛的《带经堂诗话》,袁枚的《随园诗话》等,这些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话,却是我国书话文体的开端。到了近代,影响比较大的有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和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书话逐渐规范起来;说年轻,书话到了现当代才独立成为一种文体,名著有周作人的《知堂书话》,叶灵凤的《读书随笔》《北窗读书录》,还有唐弢的《晦庵书话》等,而黄裳、姜德明等则是当代书话的大家,孙犁先生的《书衣文录》把书话写作再次推向新的阶段。
书话的写作,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作者要具有相当深厚的人文素养;二是要懂得关于书的知识;三是熟悉和了解书的作者及创作情况——新民具备了这三个条件,而且还有一个“出版人”的身份,这对他写作书话是非常有利的。所以,写出了这部厚重且文笔轻灵的书话作品。
新民爱书,喜欢读书,他在《购书》里说:“我从小爱书,自家的书不足便借之,借之不足则购之。”这句话看起来平淡,其实却是读书人大都经历过的三个阶段。尤其是在西部边远的乡村,一般来说,家里都存有几本书,然而,这远远不能够满足处在如饥似渴阅读阶段的少年的求知欲,只能借书和买书。我也有过新民这样的经历,知道这句话中蕴含着太多太多为了寻找书的人生故事。爱书,是读书人的天性,若没有这样的天性,则始终与书无缘,即是有缘也很快消失。他说,上街往往是“望商店而却步,见书店而趋步”,可见,新民与书的缘分确实不浅。
读书,犹如登塔,登得一层,眼界就宽了一层,一层一层地登,眼界就一层一层地宽,眼界宽了,想要知道的事就多了,而要知悉这些事,就得不断地读书,而“更上一层楼”的兴趣便越来越大,书也便越读越多,这是读书人永远不能逃脱的“宿命”。读了这么多书,也许有用,也许没有用,不过可以肯定地说,读书人的文化素养便日益提高,这是确凿无疑的。有了较高的文化素养,无他,至少为写书话奠定了基础,不是吗?你看新民,没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能写出这样漂亮的书话?
新民有幸,大学毕业至今一直在出版界,这对一个爱书和喜欢读书的人来说,绝对是个好去处。出版社是“生产”书的地方,新民由此而掌握了关于书的系统而规范的知识,别的不说,至少能鉴别来书好坏,这个好坏,当然是指书的内容。日常生活在书的世界里,好的书也就是内容上乘的书,先睹为快,日子久了,侵染得心灵更美了,因而,读新民的书话,总觉他涉及的人和书,都是天底下的值得“话”的人和书。他笔下的人物,有不少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都曾经叱咤风云,就是没有叱咤过风云,也能留下令人瞩目的成绩。书是人写的。新民由此认识了不少作家或者写书的朋友,知道了不少这些作家和朋友书后的故事或者掌故,这对他写书话,增添了许多有趣的题材,比如,他的《陈彦的创作经验》《怀念京夫》《乡村的吟唱者-和谷印象记》等篇什,就写得引人入胜。
写书话,要有明确的价值观和艺术观,也就是上边所说的能鉴别来书的好坏,书话家要敢于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新民的书话,其中有不少篇章是评论文章,例如《怀念海燕老师——读<青春的备忘>有忆》《行看流水坐看云——<李浩作品系列>读后感》《大美秦岭民族魂——<云横秦岭>阅后记》等,都能抓住书的核心,进行研究和探讨。他评价著名散文家孔明先生的《书中最相思》连及作者,情不自禁地说:“孔明‘他就是一个书生,一个饱读诗书的书生,一个有情有爱的可爱的书生’”——这话说得真确,孔明也是我敬重的朋友,多年交往,印证了新民所言不虚。
收到新民快递来的这部书,在微信上我发给他这样一句话“你复活了陕西的书话文体”——这句话不是随便一说,而是经过认真思考的。现在,专门从事书话写作的作家不多,新民这部著作可称之为“空谷足音”,自然有其价值和意义。
再说点题外话,我国文学史上,有专门的小说史、散文史、诗歌史和戏剧史,而没有专门的书话史。这是因为书话的总量没有其他文体大和多,要写书话史材料不足。但是书话并非没有专门写史的价值。从古到今,书话虽然不属于主流文学,却是独有其思想和艺术价值的文体,除过专门的书话作家的著作而外,几乎所有作家都参与了这个文体的写作,留下了大量值得甄别和整理的文本,如果能做这样的工作,我想,就书话写一部专门史,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好的文学研究的“补缺”工作。之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希望有人能下苦功夫,来做这样的事情。□柏峰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