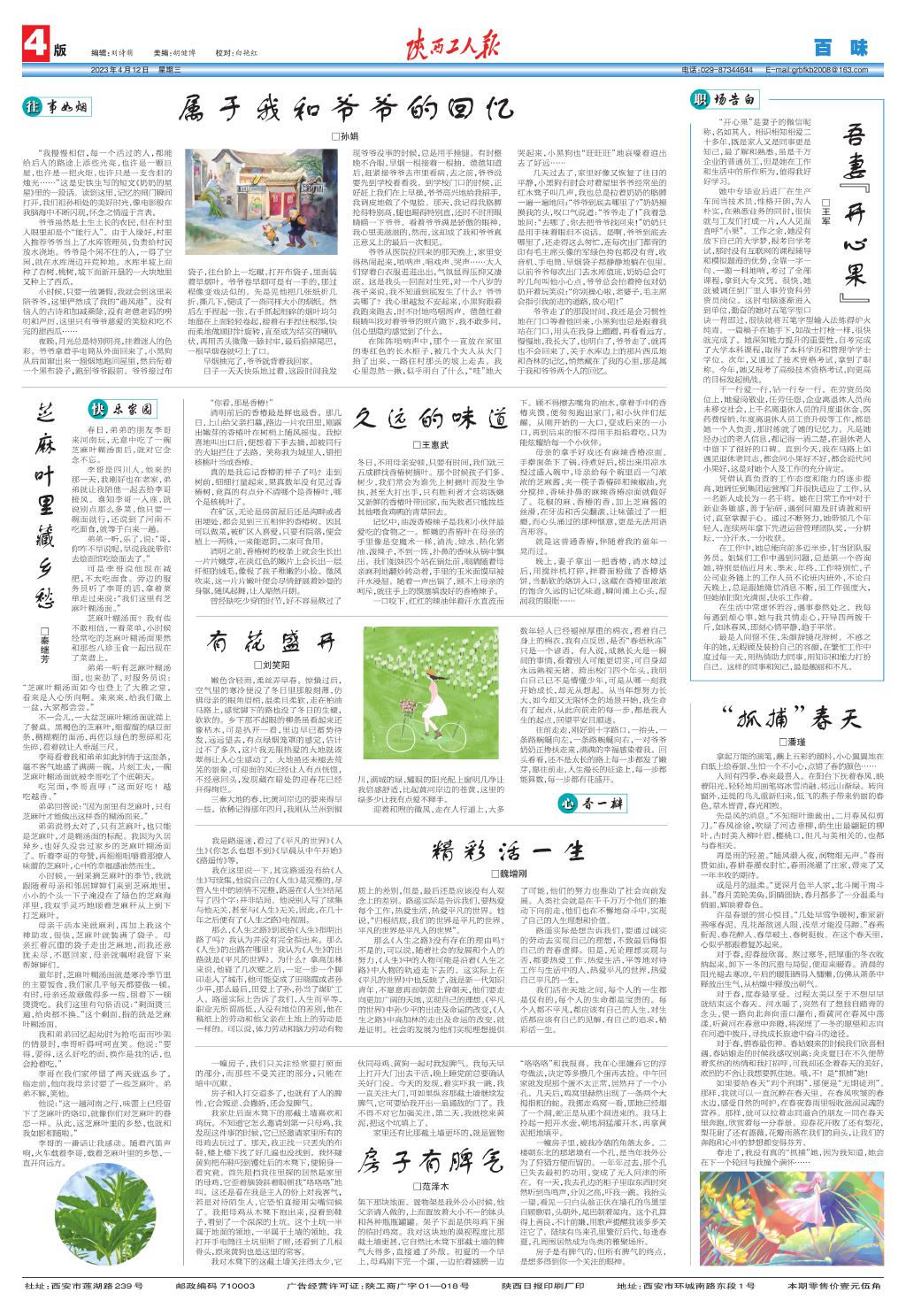属于我和爷爷的回忆
□孙娟

“我慢慢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烛光……”这是史铁生写的短文《奶奶的星星》里的一段话。读到这里,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我们祖孙相处的美好时光,像电影般在我脑海中不断闪现,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爷爷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但在村里人眼里却是个“能行人”。由于人缘好,村里人推荐爷爷当上了水库管理员,负责给村民放水浇地。爷爷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得了空闲,就在水库周边开荒种地。水库半坡上面种了杏树、桃树,坡下面新开垦的一大块地里又种上了西瓜。
小时候,只要一放暑假,我就会到这里来陪爷爷,这里俨然成了我的“避风港”。没有恼人的古诗和加减乘除,没有老爸老妈的唠叨和严厉,这里只有爷爷慈爱的笑脸和吃不完的甜西瓜……
夜晚,月光总是特别明亮,挂着迷人的色彩。爷爷拿着手电筒从外面回来了,小黑狗从后面窜出来一溜烟地跑回屋里,然后衔着一个黑布袋子,跑到爷爷跟前。爷爷接过布袋子,往台阶上一圪蹴,打开布袋子,里面装着旱烟叶。爷爷卷旱烟可是有一手的,那过程像变戏法似的。先是见他把几张纸折几折、撕几下,便成了一沓同样大小的烟纸。然后左手捏起一张,右手抓起细碎的烟叶均匀地溜在上面轻轻卷起,接着右手捏住根部,快而柔地做顺时针旋转,直至成为结实的喇叭状,再用舌头微微一舔封牢,最后掐掉尾巴,一根旱烟卷就叼上了口。
旱烟抽完了,爷爷就背着我回家。
日子一天天快乐地过着,这段时间我发现爷爷没事的时候,总是用手捶腿。有时整晚不合眼,旱烟一根接着一根抽。爸爸知道后,赶紧接爷爷去市里看病,去之前,爷爷说要先到学校看看我。到学校门口的时候,正好赶上我们在上早操,爷爷高兴地给我招手,我调皮地做了个鬼脸。那天,我记得我胳膊抡得特别高,腿也踢得特别直,还时不时用眼睛瞄一下爷爷。看着爷爷满是骄傲的眼神,我心里美滋滋的,然而,这却成了我和爷爷真正意义上的最后一次相见。
爷爷从医院拉回来的那天晚上,家里变得热闹起来,唢呐声、唱戏声、哭声……大人们穿着白衣服进进出出,气氛显得压抑又凄凉。这是我头一回面对生死,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爷爷去哪了?我心里越发不安起来,小黑狗跟着我跑来跑去,时不时地呜咽两声。爸爸红着眼睛叫我对着爷爷的照片跪下,我不敢多问,但心里隐约感觉到了什么。
在阵阵唢呐声中,那个一直放在家里的枣红色的长木柜子,被几个大人从大门抬了出来,一路往村那头的坡上走去。我心里忽然一揪,似乎明白了什么,“哇”地大哭起来,小黑狗也“旺旺旺”地哀嚎着追出去了好远……
几天过去了,家里好像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小黑狗有时会对着屋里爷爷经常坐的红木凳子叫几声,我也总是拉着奶奶的胳膊一遍一遍地问:“爷爷到底去哪里了?”奶奶摸摸我的头,叹口气说道:“爷爷走了!”我着急地问:“去哪了,你去把爷爷找回来!”奶奶只是用手抹着眼泪不说话。是啊,爷爷到底去哪里了,还走得这么匆忙,连每次出门都背的印有毛主席头像的军绿色挎包都没有背,收音机、手电筒、旱烟袋子都静静地躺在包里。以前爷爷每次出门去水库值班,奶奶总会叮咛几句叫他小心点,爷爷总会拍着挎包对奶奶开着玩笑说:“你别操心啦,老婆子,毛主席会指引我前进的道路,放心吧!”
爷爷走了的那段时间,我还是会习惯性地在门口等着他回来,小黑狗也总是跟着我站在门口,用头在我身上蹭蹭,再看看远方。慢慢地,我长大了,也明白了,爷爷走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关于水库边上的那片西瓜地和杏林的记忆,悄然藏在了我的心里,那是属于我和爷爷两个人的回忆。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孙娟

“我慢慢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烛光……”这是史铁生写的短文《奶奶的星星》里的一段话。读到这里,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我们祖孙相处的美好时光,像电影般在我脑海中不断闪现,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爷爷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但在村里人眼里却是个“能行人”。由于人缘好,村里人推荐爷爷当上了水库管理员,负责给村民放水浇地。爷爷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得了空闲,就在水库周边开荒种地。水库半坡上面种了杏树、桃树,坡下面新开垦的一大块地里又种上了西瓜。
小时候,只要一放暑假,我就会到这里来陪爷爷,这里俨然成了我的“避风港”。没有恼人的古诗和加减乘除,没有老爸老妈的唠叨和严厉,这里只有爷爷慈爱的笑脸和吃不完的甜西瓜……
夜晚,月光总是特别明亮,挂着迷人的色彩。爷爷拿着手电筒从外面回来了,小黑狗从后面窜出来一溜烟地跑回屋里,然后衔着一个黑布袋子,跑到爷爷跟前。爷爷接过布袋子,往台阶上一圪蹴,打开布袋子,里面装着旱烟叶。爷爷卷旱烟可是有一手的,那过程像变戏法似的。先是见他把几张纸折几折、撕几下,便成了一沓同样大小的烟纸。然后左手捏起一张,右手抓起细碎的烟叶均匀地溜在上面轻轻卷起,接着右手捏住根部,快而柔地做顺时针旋转,直至成为结实的喇叭状,再用舌头微微一舔封牢,最后掐掉尾巴,一根旱烟卷就叼上了口。
旱烟抽完了,爷爷就背着我回家。
日子一天天快乐地过着,这段时间我发现爷爷没事的时候,总是用手捶腿。有时整晚不合眼,旱烟一根接着一根抽。爸爸知道后,赶紧接爷爷去市里看病,去之前,爷爷说要先到学校看看我。到学校门口的时候,正好赶上我们在上早操,爷爷高兴地给我招手,我调皮地做了个鬼脸。那天,我记得我胳膊抡得特别高,腿也踢得特别直,还时不时用眼睛瞄一下爷爷。看着爷爷满是骄傲的眼神,我心里美滋滋的,然而,这却成了我和爷爷真正意义上的最后一次相见。
爷爷从医院拉回来的那天晚上,家里变得热闹起来,唢呐声、唱戏声、哭声……大人们穿着白衣服进进出出,气氛显得压抑又凄凉。这是我头一回面对生死,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爷爷去哪了?我心里越发不安起来,小黑狗跟着我跑来跑去,时不时地呜咽两声。爸爸红着眼睛叫我对着爷爷的照片跪下,我不敢多问,但心里隐约感觉到了什么。
在阵阵唢呐声中,那个一直放在家里的枣红色的长木柜子,被几个大人从大门抬了出来,一路往村那头的坡上走去。我心里忽然一揪,似乎明白了什么,“哇”地大哭起来,小黑狗也“旺旺旺”地哀嚎着追出去了好远……
几天过去了,家里好像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小黑狗有时会对着屋里爷爷经常坐的红木凳子叫几声,我也总是拉着奶奶的胳膊一遍一遍地问:“爷爷到底去哪里了?”奶奶摸摸我的头,叹口气说道:“爷爷走了!”我着急地问:“去哪了,你去把爷爷找回来!”奶奶只是用手抹着眼泪不说话。是啊,爷爷到底去哪里了,还走得这么匆忙,连每次出门都背的印有毛主席头像的军绿色挎包都没有背,收音机、手电筒、旱烟袋子都静静地躺在包里。以前爷爷每次出门去水库值班,奶奶总会叮咛几句叫他小心点,爷爷总会拍着挎包对奶奶开着玩笑说:“你别操心啦,老婆子,毛主席会指引我前进的道路,放心吧!”
爷爷走了的那段时间,我还是会习惯性地在门口等着他回来,小黑狗也总是跟着我站在门口,用头在我身上蹭蹭,再看看远方。慢慢地,我长大了,也明白了,爷爷走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关于水库边上的那片西瓜地和杏林的记忆,悄然藏在了我的心里,那是属于我和爷爷两个人的回忆。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