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中国人的原乡
——吴文莉的“西安城”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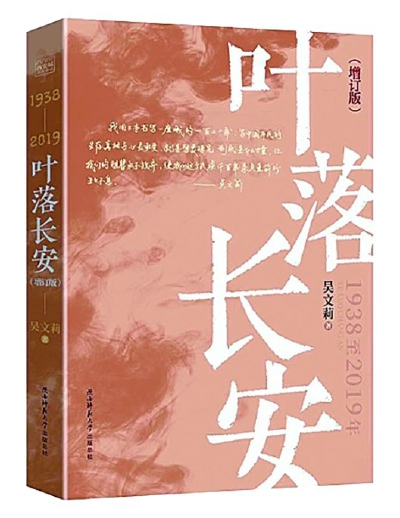
在当代陕西作家中,能够以三十年笔力与精神去追忆、书写百年西安移民史的恐怕仅有“70后”作家吴文莉。从《叶落大地》到《叶落长安》,再到《黄金城》,整个故事脉络贯穿了西安城市一百二十年的发展进程。“西安城”系列作品写的是那些因战乱、灾害而被迫远走他乡的异乡人的故事,他们是扎根在西安的山东人、河南人、河北人,他们度过了从对西安的陌生到熟悉,从隔阂到融入,最终魂归这片土地的一生。
《叶落长安》名字取自“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是吴文莉的“西安城”系列长篇小说的起端,是引领“西安城”系列作品的叙事体系。于是,我们看到了20世纪羸弱而渺小的生命个体组成的迁徙足迹在华夏的地理版图上无序地游荡,各自寻找着生命的活路与出口。“他们想要寻一块土地,安放自己的日子和灵魂,耕作、劳动,直到生命终结,就算落叶不能归根,也想叶落大地,回归土壤。”而西安,恰恰是中国人的原乡。
二十多岁的时候,吴文莉像几千年前那些深入乡间肌理收集民歌的使者,一次次往返于丰沃的关中平原腹地,在临潼、阎良乃至富平等地的山东村,从那些老人口口相传的记忆里抽丝剥茧,寻找着一百年前山东人西进冒险的传奇故事以及那些细碎泼烦的日子。那些发黄干脆的家族族谱与记忆里的时间隐藏着生命的密码。吴文莉行走乡间的脚印与一百年前那些西进的人群不谋而合。《叶落大地》中对关中大旱时饥荒的描写,对谭守东拜师学木匠手艺、学接骨手艺等的描写,让有过这些经历的“60后”“50后”都大为吃惊。正如评论家李震所言:吴文莉这种基于长期深入生活,深入观察、思考,冶炼体验强度的写作,对绝大多数沉迷于时尚、身体、欲望、消费的“70后”“80后”“90后”作家都具有启示意义。她的这种对饥饿、疼痛、死亡的极限体验让人刻骨铭心。
同样在《叶落长安》中,吴文莉试图还原的是20世纪50年代那些从河南中原大地迁徙关中平原的生命之旅,作品中几条不同的叙述场景,几条脉络有时不期相遇,有时碰撞交织。而到《黄金城》时,从河南迁徙西安城的“道北人”已经开始与城市血水相融,逐渐化作城市的一分子。
吴文莉在行走中有了一种历史意识或文化自觉,“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家是传统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场景。她敏锐地发掘了一个庭院和一个小院里的悲欢离合,将其与整个宏阔的大世界通联起来。如其所言:“我总认为,一个家庭、一个小院里的悲欢离合有时便是一个城的缩影,一个中国城市的荣辱兴衰往往便是整个中国的缩影。”
移民作为文化最活跃的载体之一,带来多元的文化,使其成为吴文莉写作的一种驱动力。吴文莉以“移民视角”揭示着西安城市如同候鸟的本质所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乡土、不同的文化与不同的血脉却在生命无望之际,风尘仆仆来到西安城,这些人中有着吴文莉的“外婆、外公”“公公、婆婆”,他们在惊慌失措的时代逃到西安城,用八十多年的时光融入这城里,渐无痕迹。时至今日,那些移民村子、堡子在历史的塑形中已经与关中平原的其他村落无异。她说她必须用文字去记载河南难民逃到这座城的传奇,把他们平常细碎的日子留在西安城的历史里。她说:“我愿意当这城忠心耿耿的书写者。”如果说,道北、小东门城墙根是西安城的缩影,那么西安又何尝不是中国城市发展进程的缩影?
无论是《叶落大地》《叶落长安》,还是《黄金城》,西安的街道小巷如一幅活生生的画卷,随着人物的脚步带着我们在历史的风尘中,观望市井生活。西安城市井字街口为作者提供了想象历史的可能性,也为我们回望这座城市的繁华与记忆提供了通道。寻常百姓家的嘘寒问暖与粗茶淡饭或许才是生活与城市的本来面貌。他们爱西安,他们要“叶落长安”,这些困境与细节却在“西安城系列”作品中逼真地呈现了出来,有入木三分、摄人魂魄之效。
吴文莉的“叶落”意象指向西安城市的变迁与人口结构,更重要的是,她从城市与人口双重结构变化中将“叶落”提升到生命的终极追问上来。我们苦苦追寻的历史记忆,除去了宏大的场面之外,更多是由无数普通人的生命悲叹构成,那些闪烁着生命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鲜活经验,在城市或现或隐的大街小巷为我们提供着重返生命与历史的深处勘探的欲望与想象,那些熙攘往来之中涌现着泥土的冰冷与寒暖,希望依旧是西安城中最为耀眼的词语。
城市化给移民来西安的“异乡人”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从居住条件、生活与工作方式以及价值观都带来改变。今天,居住在西安的河南人数以百万计,其中有很多是当年逃荒灾民的后代,他们正在影响着西安城:“小东门区域改造过后,小东门城墙里外那些多如蛛网的小巷子都没了,在大大小小的街道里形成了许多小区,几十年前逃荒来到西安小东门的这些河南人就大多住进了小区里的楼房。”
过去的记忆在他们的城市生活中并没有完全消失或被遗忘,而是以某种客观象征物存在着。西安城,无论是唐长安城,还是明长安城,都是四四方方的。城里的小巷子和小院子、城外的村庄,都是组成西安城的一个个鲜活的细胞。“西安城”是吴文莉写作的根据地,是一个载体,是一个物象、一个文学的依托。亦如学者萧云儒所说:“对上百万流落在秦地,生活了几十年几代人的河南弟兄,陕西文学终于有了一个交代,终于给了一个审美的说法。”
也基于此,“西安城”系列小说取材近乎相似,笔法和结构各有特点,既有历史宏大的背景轮廓做牵引与框架,又有移民村群体的真实生活细节做充实。从迁入到融入,再到落地生根的过程是生命重塑的艰辛历程,在这个过程中这群“异乡人”与这座城融为一体,生命血肉与精神皆复苏在此,“西安”城于是成了他们的家园与故土的根底,原乡已经在一代代生命记忆中成了传奇。□王刚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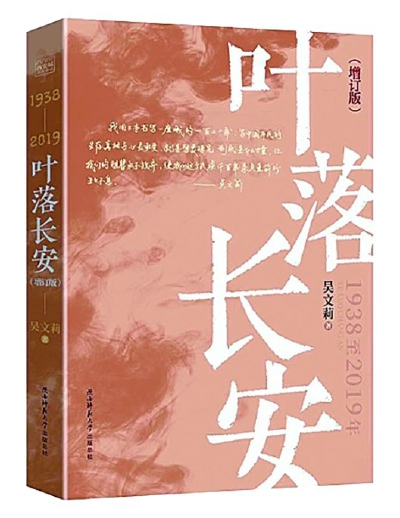
在当代陕西作家中,能够以三十年笔力与精神去追忆、书写百年西安移民史的恐怕仅有“70后”作家吴文莉。从《叶落大地》到《叶落长安》,再到《黄金城》,整个故事脉络贯穿了西安城市一百二十年的发展进程。“西安城”系列作品写的是那些因战乱、灾害而被迫远走他乡的异乡人的故事,他们是扎根在西安的山东人、河南人、河北人,他们度过了从对西安的陌生到熟悉,从隔阂到融入,最终魂归这片土地的一生。
《叶落长安》名字取自“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是吴文莉的“西安城”系列长篇小说的起端,是引领“西安城”系列作品的叙事体系。于是,我们看到了20世纪羸弱而渺小的生命个体组成的迁徙足迹在华夏的地理版图上无序地游荡,各自寻找着生命的活路与出口。“他们想要寻一块土地,安放自己的日子和灵魂,耕作、劳动,直到生命终结,就算落叶不能归根,也想叶落大地,回归土壤。”而西安,恰恰是中国人的原乡。
二十多岁的时候,吴文莉像几千年前那些深入乡间肌理收集民歌的使者,一次次往返于丰沃的关中平原腹地,在临潼、阎良乃至富平等地的山东村,从那些老人口口相传的记忆里抽丝剥茧,寻找着一百年前山东人西进冒险的传奇故事以及那些细碎泼烦的日子。那些发黄干脆的家族族谱与记忆里的时间隐藏着生命的密码。吴文莉行走乡间的脚印与一百年前那些西进的人群不谋而合。《叶落大地》中对关中大旱时饥荒的描写,对谭守东拜师学木匠手艺、学接骨手艺等的描写,让有过这些经历的“60后”“50后”都大为吃惊。正如评论家李震所言:吴文莉这种基于长期深入生活,深入观察、思考,冶炼体验强度的写作,对绝大多数沉迷于时尚、身体、欲望、消费的“70后”“80后”“90后”作家都具有启示意义。她的这种对饥饿、疼痛、死亡的极限体验让人刻骨铭心。
同样在《叶落长安》中,吴文莉试图还原的是20世纪50年代那些从河南中原大地迁徙关中平原的生命之旅,作品中几条不同的叙述场景,几条脉络有时不期相遇,有时碰撞交织。而到《黄金城》时,从河南迁徙西安城的“道北人”已经开始与城市血水相融,逐渐化作城市的一分子。
吴文莉在行走中有了一种历史意识或文化自觉,“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家是传统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场景。她敏锐地发掘了一个庭院和一个小院里的悲欢离合,将其与整个宏阔的大世界通联起来。如其所言:“我总认为,一个家庭、一个小院里的悲欢离合有时便是一个城的缩影,一个中国城市的荣辱兴衰往往便是整个中国的缩影。”
移民作为文化最活跃的载体之一,带来多元的文化,使其成为吴文莉写作的一种驱动力。吴文莉以“移民视角”揭示着西安城市如同候鸟的本质所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乡土、不同的文化与不同的血脉却在生命无望之际,风尘仆仆来到西安城,这些人中有着吴文莉的“外婆、外公”“公公、婆婆”,他们在惊慌失措的时代逃到西安城,用八十多年的时光融入这城里,渐无痕迹。时至今日,那些移民村子、堡子在历史的塑形中已经与关中平原的其他村落无异。她说她必须用文字去记载河南难民逃到这座城的传奇,把他们平常细碎的日子留在西安城的历史里。她说:“我愿意当这城忠心耿耿的书写者。”如果说,道北、小东门城墙根是西安城的缩影,那么西安又何尝不是中国城市发展进程的缩影?
无论是《叶落大地》《叶落长安》,还是《黄金城》,西安的街道小巷如一幅活生生的画卷,随着人物的脚步带着我们在历史的风尘中,观望市井生活。西安城市井字街口为作者提供了想象历史的可能性,也为我们回望这座城市的繁华与记忆提供了通道。寻常百姓家的嘘寒问暖与粗茶淡饭或许才是生活与城市的本来面貌。他们爱西安,他们要“叶落长安”,这些困境与细节却在“西安城系列”作品中逼真地呈现了出来,有入木三分、摄人魂魄之效。
吴文莉的“叶落”意象指向西安城市的变迁与人口结构,更重要的是,她从城市与人口双重结构变化中将“叶落”提升到生命的终极追问上来。我们苦苦追寻的历史记忆,除去了宏大的场面之外,更多是由无数普通人的生命悲叹构成,那些闪烁着生命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鲜活经验,在城市或现或隐的大街小巷为我们提供着重返生命与历史的深处勘探的欲望与想象,那些熙攘往来之中涌现着泥土的冰冷与寒暖,希望依旧是西安城中最为耀眼的词语。
城市化给移民来西安的“异乡人”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从居住条件、生活与工作方式以及价值观都带来改变。今天,居住在西安的河南人数以百万计,其中有很多是当年逃荒灾民的后代,他们正在影响着西安城:“小东门区域改造过后,小东门城墙里外那些多如蛛网的小巷子都没了,在大大小小的街道里形成了许多小区,几十年前逃荒来到西安小东门的这些河南人就大多住进了小区里的楼房。”
过去的记忆在他们的城市生活中并没有完全消失或被遗忘,而是以某种客观象征物存在着。西安城,无论是唐长安城,还是明长安城,都是四四方方的。城里的小巷子和小院子、城外的村庄,都是组成西安城的一个个鲜活的细胞。“西安城”是吴文莉写作的根据地,是一个载体,是一个物象、一个文学的依托。亦如学者萧云儒所说:“对上百万流落在秦地,生活了几十年几代人的河南弟兄,陕西文学终于有了一个交代,终于给了一个审美的说法。”
也基于此,“西安城”系列小说取材近乎相似,笔法和结构各有特点,既有历史宏大的背景轮廓做牵引与框架,又有移民村群体的真实生活细节做充实。从迁入到融入,再到落地生根的过程是生命重塑的艰辛历程,在这个过程中这群“异乡人”与这座城融为一体,生命血肉与精神皆复苏在此,“西安”城于是成了他们的家园与故土的根底,原乡已经在一代代生命记忆中成了传奇。□王刚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