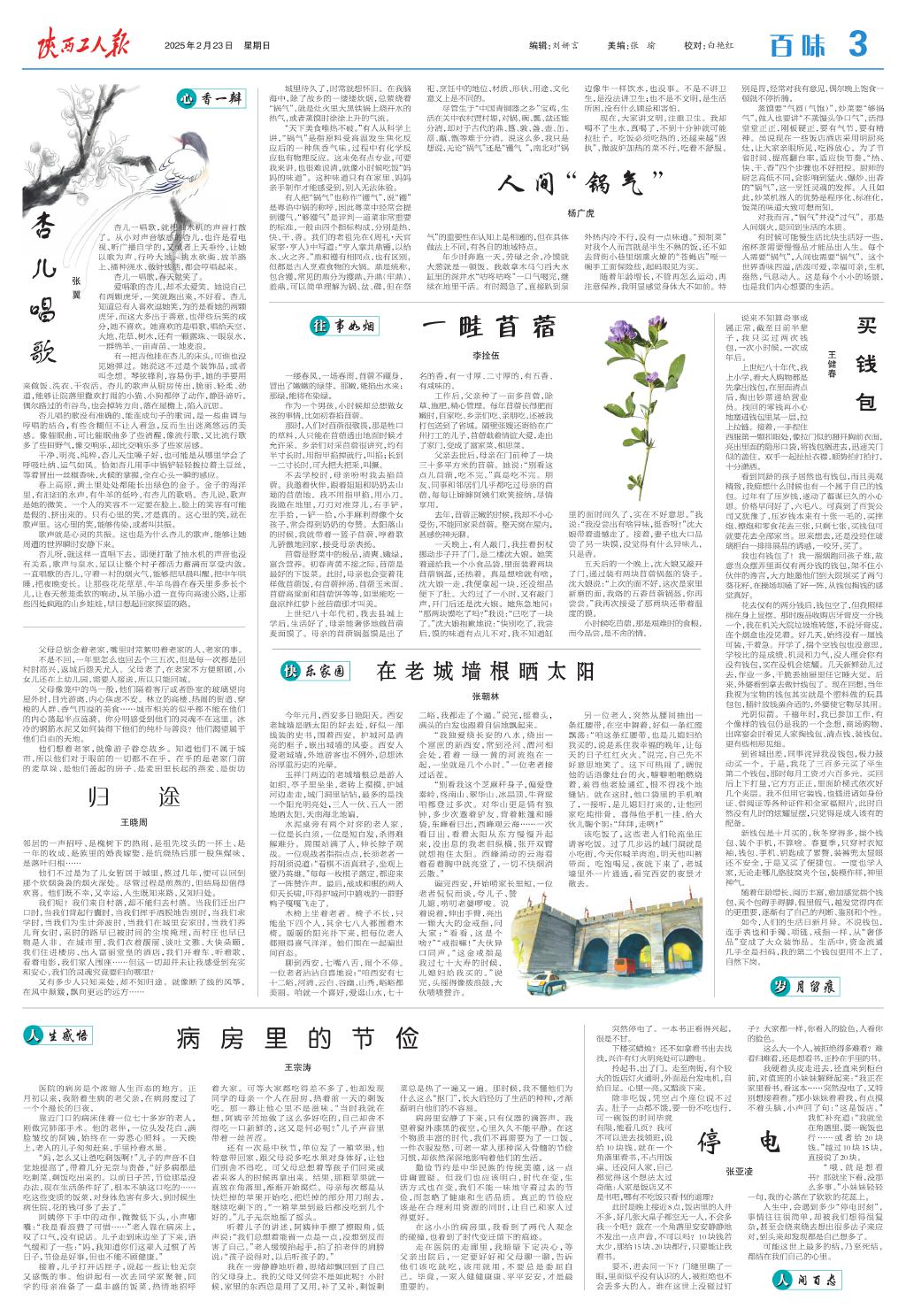一畦苜蓿
李拴伍

一缕春风、一场春雨,苜蓿不藏身,冒出了嫩嫩的绿芽。那嫩,能掐出水来;那绿,能将布染绿。
作为一个男孩,小时候却总想做女孩的事情,比如初春掐苜蓿。
那时,人们对苜蓿很敬畏,那是牲口的草料,人只能在苜蓿透出地面时候才允许采。乡亲们对采苜蓿很讲究,约有半寸长时,用指甲掐掉就行,叫掐;长到一二寸长时,可大把大把采,叫撅。
不去学校时,母亲吩咐我去掐苜蓿。我邀着伙伴,跟着姐姐和奶奶去山坳的苜蓿地。我不用指甲掐,用小刀。我跪在地里,刀刃对准芽儿,右手铲,左手拾,一铲一拾,小手麻利得像个女孩子,常会得到奶奶的夸赞。太阳落山的时候,我就带着一篮子苜蓿,哼着歌儿骄傲地回家,接受母亲表扬。
苜蓿是野菜中的极品,清爽、嫩绿,富含营养。初春青黄不接之际,苜蓿是最好的下饭菜。此时,母亲也会变着花样做苜蓿饭,有苜蓿拌汤、苜蓿玉米面、苜蓿高粱面和苜蓿饼等等,如果能吃一盘凉拌红萝卜丝苜蓿那才叫美。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去县城上学后,生活好了,母亲能奢侈地做苜蓿麦面馍了。母亲的苜蓿锅盔馍是出了名的香,有一寸厚、二寸厚的,有五香、有咸味的。
工作后,父亲种了一亩多苜蓿,除草、施肥,精心管理。每年苜蓿长得肥而嫩时,自家吃、乡亲们吃、亲朋吃,还被我打包送到了省城。隔壁张嫂还寄给在广州打工的儿子,苜蓿载着情谊大爱,走出了家门,变成了富家菜、相思菜。
父亲去世后,母亲在门前种了一块三十多平方米的苜蓿。她说:“别看这点儿苜蓿,吃不完。”真是吃不完。朋友、同事和邻居们几乎都吃过母亲的苜蓿,每每让婶婶阿姨们欢笑接纳,尽情享用。
去年,苜蓿正嫩的时候,我却不小心受伤,不能回家采苜蓿。整天窝在屋内,甚感伤神无聊。
一天晚上,有人敲门,我拄着拐杖挪动步子开了门,是二楼沈大娘。她笑着递给我一个小食品袋,里面装着两块苜蓿锅盔,还热着。真是想啥就有啥,沈大娘一走,我便拿起一块,还没细品便下了肚。大约过了一小时,又有敲门声,开门后还是沈大娘。她焦急地问:“那两块馍吃了吗?”我说:“已吃了一块了。”沈大娘抱歉地说:“快别吃了,我尝后,馍的味道有点儿不对,我不知道缸里的面时间久了,实在不好意思。”我说:“我没尝出有啥异味,挺香呀!”沈大娘带着遗憾走了。接着,妻子也大口品尝了另一块馍,没觉得有什么异味儿,只是香。
五天后的一个晚上,沈大娘又敲开了门,递过装有两块苜蓿锅盔的袋子。沈大娘说:“上次的面不好,这次是家里新磨的面,我烙的五香苜蓿锅盔,你再尝尝。”我再次接受了那两块还带着温度的馍。
小时候吃苜蓿,那是艰难时的食粮,而今品尝,是不舍的情。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李拴伍

一缕春风、一场春雨,苜蓿不藏身,冒出了嫩嫩的绿芽。那嫩,能掐出水来;那绿,能将布染绿。
作为一个男孩,小时候却总想做女孩的事情,比如初春掐苜蓿。
那时,人们对苜蓿很敬畏,那是牲口的草料,人只能在苜蓿透出地面时候才允许采。乡亲们对采苜蓿很讲究,约有半寸长时,用指甲掐掉就行,叫掐;长到一二寸长时,可大把大把采,叫撅。
不去学校时,母亲吩咐我去掐苜蓿。我邀着伙伴,跟着姐姐和奶奶去山坳的苜蓿地。我不用指甲掐,用小刀。我跪在地里,刀刃对准芽儿,右手铲,左手拾,一铲一拾,小手麻利得像个女孩子,常会得到奶奶的夸赞。太阳落山的时候,我就带着一篮子苜蓿,哼着歌儿骄傲地回家,接受母亲表扬。
苜蓿是野菜中的极品,清爽、嫩绿,富含营养。初春青黄不接之际,苜蓿是最好的下饭菜。此时,母亲也会变着花样做苜蓿饭,有苜蓿拌汤、苜蓿玉米面、苜蓿高粱面和苜蓿饼等等,如果能吃一盘凉拌红萝卜丝苜蓿那才叫美。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去县城上学后,生活好了,母亲能奢侈地做苜蓿麦面馍了。母亲的苜蓿锅盔馍是出了名的香,有一寸厚、二寸厚的,有五香、有咸味的。
工作后,父亲种了一亩多苜蓿,除草、施肥,精心管理。每年苜蓿长得肥而嫩时,自家吃、乡亲们吃、亲朋吃,还被我打包送到了省城。隔壁张嫂还寄给在广州打工的儿子,苜蓿载着情谊大爱,走出了家门,变成了富家菜、相思菜。
父亲去世后,母亲在门前种了一块三十多平方米的苜蓿。她说:“别看这点儿苜蓿,吃不完。”真是吃不完。朋友、同事和邻居们几乎都吃过母亲的苜蓿,每每让婶婶阿姨们欢笑接纳,尽情享用。
去年,苜蓿正嫩的时候,我却不小心受伤,不能回家采苜蓿。整天窝在屋内,甚感伤神无聊。
一天晚上,有人敲门,我拄着拐杖挪动步子开了门,是二楼沈大娘。她笑着递给我一个小食品袋,里面装着两块苜蓿锅盔,还热着。真是想啥就有啥,沈大娘一走,我便拿起一块,还没细品便下了肚。大约过了一小时,又有敲门声,开门后还是沈大娘。她焦急地问:“那两块馍吃了吗?”我说:“已吃了一块了。”沈大娘抱歉地说:“快别吃了,我尝后,馍的味道有点儿不对,我不知道缸里的面时间久了,实在不好意思。”我说:“我没尝出有啥异味,挺香呀!”沈大娘带着遗憾走了。接着,妻子也大口品尝了另一块馍,没觉得有什么异味儿,只是香。
五天后的一个晚上,沈大娘又敲开了门,递过装有两块苜蓿锅盔的袋子。沈大娘说:“上次的面不好,这次是家里新磨的面,我烙的五香苜蓿锅盔,你再尝尝。”我再次接受了那两块还带着温度的馍。
小时候吃苜蓿,那是艰难时的食粮,而今品尝,是不舍的情。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